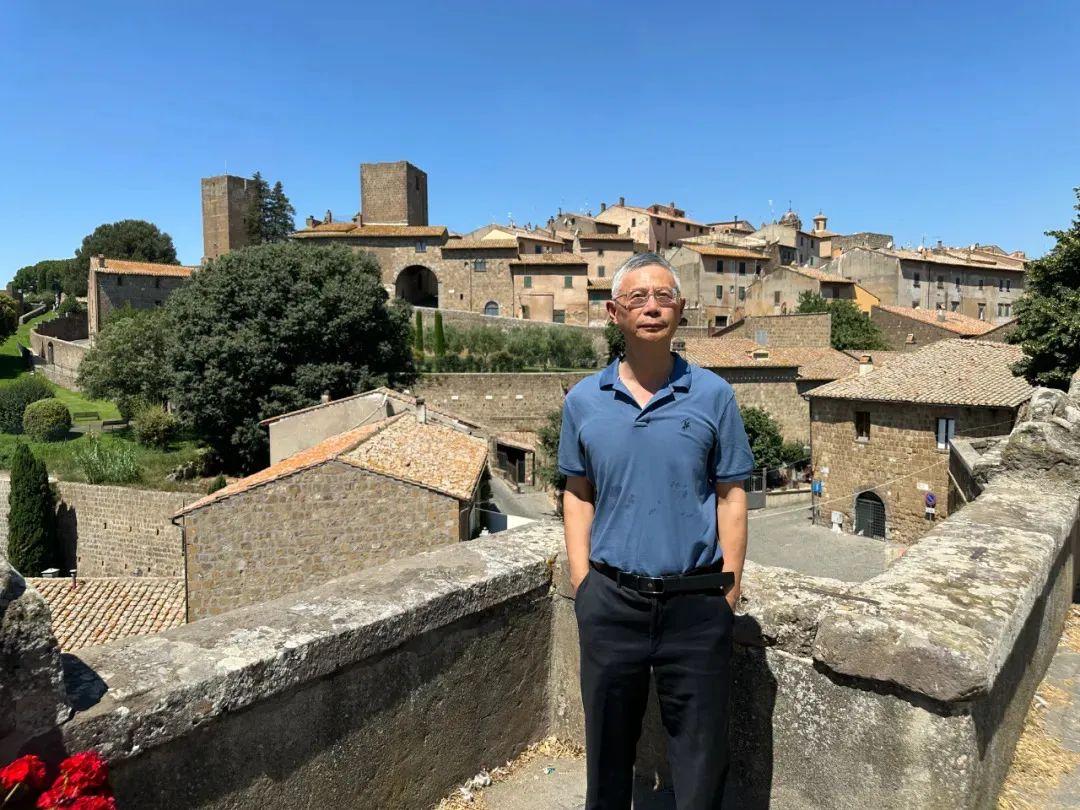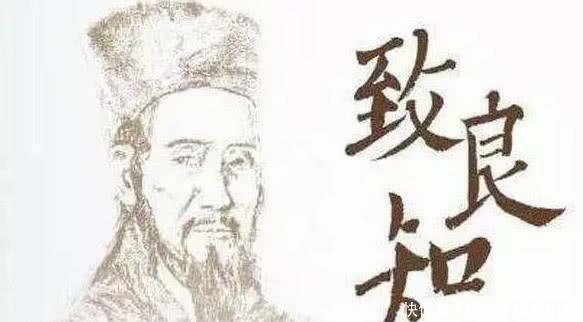作者简介:邓国坤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25年11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王阳明的时间哲学是颇具价值却尚待研究的领域。例如未发与已发时间属于何种性质的时间?它是由何种意识构造的?除了未发与已发时间之外,是否存在更原本的时间流?这种原时间流源自于何种意识?通过时间现象学的视域、方法和理论研究上述问题,不仅可以可以推进与完善阳明学研究,也有助于现象学与阳明学进一步的比较、互鉴与融通。
一、时间被构造与被意识:良知
在探讨阳明学的时间类型之前,必须先要研究比时间更为原本的问题,亦即时间是如何被构造或者被意识到?倪梁康指出时间源于意识的不断活动(《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2页),而原自我是意识活动的本源与构造者(《缘起与实相》,商务印书馆,第13页)。原时间流或内时间即是意识流的形式,是被内时间意识所察觉的。在意识流动时,内时间意识“非意向的、非对象化的方式伴随意识流行一起进行”的“对意识流动的察觉”(《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1页)。在阳明学中,良知具备原自我与内时间意识的义涵或功能。
在阳明学中,良知是意识流的本源与构造者。阳明指出,良知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具体而言,良知生成与构造感知、情感与意欲等意识,以及天地万物在内的一切事物。例如“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王阳明全集·卷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王阳明全集·卷三》)。于是,良知构造了“彻头彻尾,无始无终”的生生不息的意识流或意念流。当此意念流生成之后,内时间也与之同时形成了。
良知不仅能够构造时间,也能够意识或证知时间。阳明的“自知”与“独知”思想不仅仅具备道德自证分或特殊的自身意识,也具备内时间意识的义涵。首先,作为自知和独知的良知能够同时知悉所有意念及其发生的。例如“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其次,良知的自知与独知能够“对意识流动的察觉”。例如“动无不和,即静无不中。而所谓寂然不动之体,当自知之矣”中,良知本体能够对动静(发用流行、即意识活动)同时证知。又如“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中,独知能够对有事与无事时间及其意识内容的同时证知。
综上所述,阳明的良知是构造意识流与时间的原自我,以及对时间及其意识内容同时证知的内时间意识。通过对于良知此二种义涵的分析,可以解决阳明时间被构造与被意识的问题,亦即为下文内时间的形成与主观时间的构造奠定基础。
二、原自我构造的内时间:生生不息
不断流动的意识形成了活的当下以及过去、当下、未来三种时间,“意识无须超出自身就可以知道当下会不断地过去,成为回忆的内容,而未来会不可阻止的到来,成为当下的生活”(《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1页)。在阳明学中,在作为原自我的良知的构造下,一种生生不息、彻头彻尾、无始无终的意念流得以生成,而其中“生生不息”即是意念不断生成的原时间或内时间,被生生不息生成的意念作为意识内容。
在阳明学中,生生不息时间流曾被多次论述。除了上述的良知之生生不息话语之外,还有“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王阳明全集·卷一》);“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王阳明全集·卷三》)。在上述话语中,阳明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人生论等不同角度阐述了“生生不息”的内时间,而且以木之生发、人心生意的比喻说明了“生生不息”的内时间。此种生生不息实质上是说明人类意念或意识生生不息的流动。当人类意念源源不断地生成,亦即是原时间流或内时间是生生不息的。当然,生生不息的原时间得以被意识或证知,源于良知的“自知”与“独知”的功能。由于自知与独知对于意念流与内时间的恒常的、同时的、非对象、非反思的察觉,意念流与内时间方才被证知。此乃内时间的结构与特征被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关于内时间的本质特征,胡塞尔时间现象学强调活的当下以及“原印象、滞留、前摄”的内时间意识的基本结构,而阳明强调主张生生不息,无始无终的内时间特征。就不同处而言,两者似乎存在“原印象、滞留、前摄”的三分特征与“念念相续”的一体性的差异。阳明的这种内时间特征与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心性论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中国哲学主张生生不息、无始无终的宇宙论,以及生生不息,念念不断的心性论。但是阳明学与现象学的内时间特征也具有一致性,因为他们都主张“意识在指向对象的同时,本身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0页),以及“更新涌现的意识内容也会以此方式让位给更新的意识内容”(《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2页)。
三、反思构造的主观时间:未发与已发
在现象学中,时间分为三种,分别为内时间、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主观时间便是“通过反思而构造起来的时间”(《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5页),“是意识通过对自己的原流状态的反思而把握到的个体的意识体验的时间”(《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5页)。阳明学的未发与已发时间便是这种通过反思而构造起来的时间。例如阳明指出,“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王阳明全集·卷三》)此处的“使人自思得之”,“落在后儒见解”正是强调主观时间的“反思性”,以及通过反思而构造的时间性,而“未发与已发”则是一种反思而构造的主观时间。
关于有无未发与已发的问题,乃是阳明学时间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因为阳明一方面提出了“未发与已发”时间,但同时提出了“无未发与已发”时间。例如“先生曰:‘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可谓无,既扣不可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王阳明全集·卷三》)在上述话语中,阳明提出了关于“未发与已发”时间与“无未发与已发”两种时间。理解这两种时间不仅对于阳明时间哲学至关重要,而且是把握阳明学的核心结构的关键环节。
“未发与已发”时间乃是主观时间。由于阳明非常重视“良知发用”,尤其是“意念之发”。当阳明以反思意识对良知发用或意念之发进行回忆与分析,其思维重心便落在了“发”上面。在分析、判断、想象的思维活动中,“发”自然成为区分不同意识的中心,以及划分不同意识流阶段的界限。于是,在“发”之前为未发阶段,在“发”之后为已发阶段。然后,阳明以未发与已发描述与说明良知未曾生成意念和已经生成意念两个阶段。所谓未发,是指良知尚未生成意念的时间;所谓已发,是指良知已经生成意念的时间。其实良知是不断地生成意念,于是在原时间流上是生生不息的。而由于阳明注重良知是否生成或发用意念的反思,于是形成了“未发与已发”的主观时间。
不同现象学的长短之分,阳明学要注重先后之别。在现象学中,“内意识始终与此方式流动,一边前行,一边下坠,本身没有长短快慢的分别。时间的长与段、快与慢是通过个体反思而构造起来的主观时间”的特征,或者“长短之分”是主观时间的基本特征(《意识现象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15页)。在阳明学中,由于阳明重视良知是否发用,或者发用的过程,于是未发与已发的先后之分成为了阳明学主观时间的基本特征。未发与已发乃是对发用之前后或先后的反思性构造,其指向良知发用的先与后。阳明学的先后之分的主观时间性与现象学的长短之分,都是对于个体反思之后的时间性,都强调了个体反思的思维特征乃是背后的文化特性。阳明的思维或文化特性是一种体用论特征,以本体的发用为思考中心,于是产生了未发与已发的先后之分的主观时间特性。
“无未发与已发”时间是指“生生不息”的内时间。在区分未发与已发时间的同时,阳明去强调无未发已发的生生不息时间。为何无未发与已发是生生不息时间?原因有二。一是,此处的“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都是指向良知本体的。而良知本身是无未发已发之分,或者说良知是无或超越未发与已发。二是,良知发用的原时间流是生生不息的,原本是没有未发已发之分。结合以上两点,阳明此处话语所指的是良知的未发已发时间与无未发已发时间,其中的无未发已发时间应是生生不息的内时间。
四、两类时间的统一
上述阳明提出了两种时间,分别为无未发已发的生生不息时间,以及未发与已发时间的主观时间,那么这两种时间的如何在阳明学中得以统一呢?其实,阳明是在“体用”视域下进行的未发已发与无未发已发的划分。在“用”的视角而言,良知本体有未发之时以及已发之时,例如未发谓之中,已发谓之和;未发为性,已发为心等等。因为用即发用,发用可分为未发之时与已发之时。所以在用的视角而言,确实可以分为未发之时与已发之时。在“体”的视角而言,良知本体虽然在未发之时谓之中,在已发之时谓之和,或者在未发之时谓之性,在已发之时谓之心,但是中、和、性、心是一是异?是一是多?在阳明学界,学人普遍认为中、和、性、心是异名而实一,义多而体一;绝对不会被认为有多个本体。这既是阳明学人,也是阳明自身的常论,例如阳明常言知行合一、心性合一、理气合一、道器合一。此外,就本体的自身概念而言,它是相对于变易的发用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否则本体就不能被称为本体。所以,作为本体的良知是没有未发与已发之分的,只是在发用情况中存有未发与已发之分。综上所述,就体的视角而言,没有未发之时与已发之时的区别。
但如果要对此二种时间作进一步的比较的话,那么以“用”为视角构建的未发与已发时间,是相对的时间。因为相对于发用而言,在“本体”视域下的无未发与已发之时乃是绝对的时间。其次,无未发已发之时是一种“永恒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是一种无分动静、寂感、有无、未发已发的时间;而且是不会变化的、始终如一的,无论在任何时候和处境中皆是如此。根本而言,这种时间建立在永恒不变的本体之中,由于本体不变如一,因此这种本体的时间也是不变如一的。另一方面,由于本体时间无变化,也就无必要强调未发与已发,也不需要构建未发之时和已发之时的先后时态。
在“体用论”的视域下,阳明既承认“用”视域下的已发之时与未发之时,也重视“体”视域下的无未发与已发之时。而由于体用不二,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的缘故,“无未发与已发之时”与“已发与未发之时”两种时态都可以被统一于体用论之中,因而也被圆融的存在于阳明学之中。正如本体存在与显现与发用之中,本体时间存在或显现于发用时间之中,亦即“无未发与已发”存在与显现于“未发与已发”之中。
五、结 语
良知是构造意识流与原时间流的原自我,也是时间及其意识内容被同时证知的内时间意识。由于上述良知的两种义涵或功能,时间得以被构造与被意识。在作为原自我的良知的构造下,一种生生不息、彻头彻尾、无始无终的意念流得以生成,而其中“生生不息”即是意念不断生成的原时间或内时间。不同于现象学内时间的“原印象、滞留、前摄”的三分特征,阳明内时间强调“念念相续”的一体性。由于对良知发用或意念之发进行反思,未发与已发的主观时间被构造。所谓未发,是指良知尚未生成意念的时间;所谓已发,是指良知已经生成意念的时间。不同现象学的长短之分,阳明主观时间强调先后之别。生生不息的内时间属于本体时间,未发与已发属于发用时间。在“体用论”的视域下,阳明既承认“用”视域下的已发之时与未发之时,也重视“体”视域下的无未发与已发之时。而由于体用不二,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的缘故,“无未发与已发之时”与“已发与未发之时”两种时态都可以被统一于体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