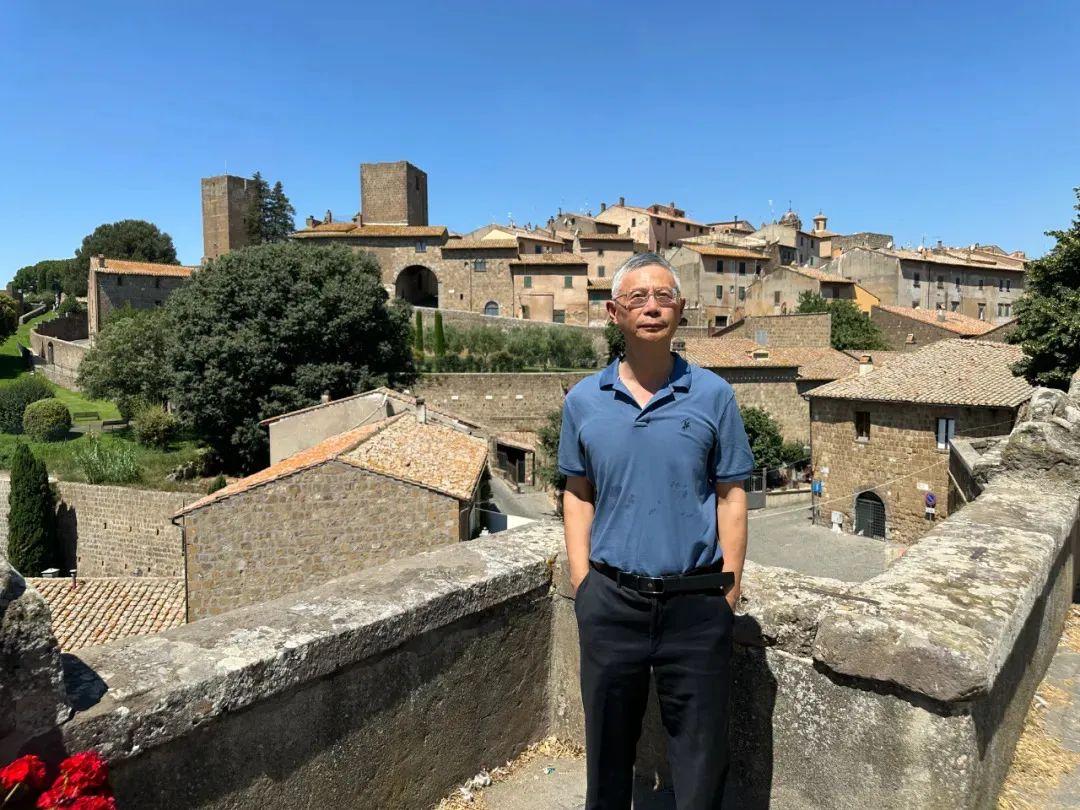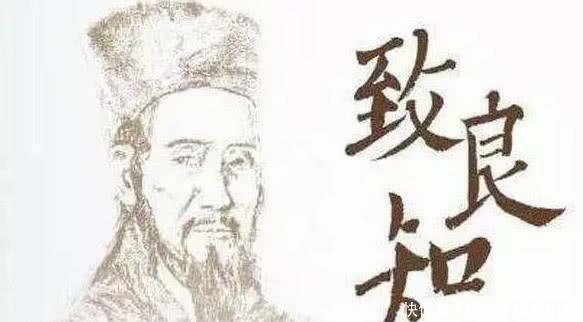李承贵教授
摘 要
“致良知”是王阳明学问的头脑,是核心所在。所谓“致良知”大致可从内容、条件、效应三个向度加以认识和把握。就其内容言,约有本体义、工夫义、实践义三个层次,本体义具体表现为种植善根、积蓄善德、中和自然,工夫义具体表现为自省修为、辨别善恶、去除私意,实践义具体表现为见诸行为、物得其理、推扩善体,因而“致良知”在内容上是由本体、工夫、实践三个层次构成的有机体系。就其条件言,约有“工夫不断成熟”“排除私心杂念”“持续专心致志”“因人施行教法”“分寸适宜至上”等,从而为“致良知”提供经验性基础。就其效应言,则包括“可应对千变万化之事象”“可助人实现成为圣贤之理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推行万物一体之仁”“可以治疗消极之心态”“可以抵御声色名利之诱惑”“可以吸纳并为科学知识腾出空间”等,从而全面展示“致良知”的效应。由此可见,王阳明“致良知”实际上呈现为三重境界:内容的境界,此即“致良知”的事实性存在;条件的境界,此即“致良知”的方法性存在;效应的境界,此即“致良知”的意义性存在,如此三重境界交相辉映,所构建的便是王阳明所期待的理想社会。进言之,“致良知”是本体与工夫、理想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体,它不仅象征着王阳明理想之纯粹,亦反映了王阳明通向理想之艰辛。
阅读导引
一、致良知内容的多重性
二、致良知条件的多样性
三、致良知效应的多向性
王阳明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关于“致良知”的内容,学界已有多种论述,这里罗列部分代表性观点。钱穆说:“致良知是一种积极向外工夫,只管把自家现前的一点良心实实落落地向外面事事物物上推送出去。”冯友兰说:“要穷人理就要尽量发挥‘良知’的作用,这就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牟宗三说:“‘致良知’是把良知之天理或良知所觉之是非善恶不让它为私欲所间隔而充分地把它呈现出来以使之见于行事,即成道德行为。”劳思光认为,“致良知”就是成德,他说:“‘良知’为人心本有之能力,人能扩充或实现此能力于行为生活中,则即是‘成德’。由此,从工夫着手处看,初有工夫,便是在‘致’良知;而从德性之完成看,则最高成就亦不过是‘致’其良知。故‘致良知’乃彻上彻下之工夫。”陈来认为,“致良知”有两义,一个是“至极义”,“就是把心之良知‘扩充到底’”,一个是“实行义”,“致良知就是将此准则(道德准则)诉诸实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致’就是行”。杨国荣说:“致良知既表现为从先天的道德本原走向现实的德性,又意味着化本然之知为明觉之知。”这些论述不尽相同,析而言之约有三义:一是将良知由内向外推的工夫;二是将良知落实于日用生活之中;三是扩充良知以成就美德。这些观点无疑极具参考价值。但王阳明“致良知”内容之丰富、方式之复杂、影响之广泛,远不在此。因而需要作更深入、更广泛、更严谨的讨论。
一、致良知内容的多重性
以往关于王阳明“致良知”内涵的分析与概括,或成就德性,或修行工夫,或推向物事而善化之,这些概括都具有启发性,但都似太简略。这里拟从本体、工夫、实践三个向度考察王阳明“致良知”的内涵。
1.致良知的本体向度。所谓“致良知”的本体向度,即从本体意义上认识“致良知”的内涵。就本体向度看,“致良知”约有三方面的意涵。其一是种植善根。良知内涵之一是至善本体,阳明说:“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这个至善本体完满无缺,是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是善的种子,因而“致良知”便是种植、固牢善根。阳明说:“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什么叫“有根本”的学问?就是在“格物”上持续努力,日日长进,时间越长越精明,从而根牢本固。而“无根本”的学问,虽外面修饰光滑亮丽,但终会放倒,虽暂时鲜好,但终必憔悴。“致良知”是“有根本”的学问,因为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则是“无根本”的学问,因为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阳明说:“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因此,由于良知汇集了所有的理义,集中了所有的良善,因而良知也是肥沃的土壤,营养丰富,从而从根基上对“心”进行滋养。因此,“致良知”是善根的种植,“随处体认天理”则是茂盛枝叶的作为。其二是积蓄善德。孟子“集义”的另一个含义,便是累积善。朱熹说:“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集义”,因而“致良知”有积累善德之意。阳明说:“若平日能集义,则浩然之气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诐淫邪遁之词皆无所施于前矣。况肯自以为惭乎!集义只是致良知。”致良知就是“集义”,“心”之平和、舒适,便是“义”。阳明说:“录善人以自勉,此亦多闻多见而识,乃是致良知之功。”如果平时坚持集义,使浩然之气达到至大至公之状态,充塞天地,就不会被富贵淫染、不会被贫贱移易、不会被威武屈服,而且能够辨别诐淫邪遁之词,此非不为积善?因而“致良知”就是累积善德。“致良知”所以是积善,还因为能够在面对毁誉得失时超越之而泰然自若,阳明说:“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如果一个人真正将良知付诸实践,那么,赞誉或诋毁都无法进入他的内心,都无法影响他的品质,反而他的善良会不断增加。其三是中和自然。王阳明认为,良知即知得过、不及处,他说:“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中和”本质上是恰到好处,是适宜,“集义”不仅是积累善德,而且是使事为适宜、通达成功,阳明说:“集义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为义,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因而“致良知”也意味着适宜,就是该如此即如此,没有任何勉强、做作。阳明说:“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所谓“心得其宜”,就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没有任何勉强,没有任何扭捏,顺其自然。这样,“致良知”也是一种人生态度。阳明说:“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自不安。凡认贼作子者,缘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体认,所谓‘虽不中,不远矣’。”这种人生态度能做到应抛弃富贵便抛弃富贵、应服从父兄即服从父兄,也就是“中和自然”。但如果执着富贵、沉迷亲情,此即夹带私意,有了私意便不是“致良知”,亦不是“中和自然”。
2.致良知的工夫向度。所谓“致良知”的工夫向度,即从工夫意义上认识“致良知”的内涵。就工夫向度看,“致良知”约有三方面的意涵。其一是自省修为。阳明说:“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戒慎于不睹、恐惧于不闻,便是慎独的工夫,《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第一章)即说,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能够保持谨慎警惕,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深怀敬畏戒惧,而不胡作非为。因此,“致良知”就是一种戒慎恐惧工夫。王阳明曾说:“谨独即是致良知。”“谨独”即在独处时保持高度的警觉和自律,谨慎不苟,所以是一种工夫。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谨独”,那么“致良知”自然也是慎独工夫。在王阳明这里,“致良知”工夫也体现在日用庸常的合礼言行中,将善体或良知贯注于生活,便是修行工夫。阳明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儿童洒扫应对就是致其良知,嬉笑中见了长者便鞠躬,也是致其良知。童子自由、童子格物是童子的“致良知”,从而说明“致良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也不分男女,无分老少,既然无处不是致良知,所以无处不是工夫。阳明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就是说,所以有鸢飞鱼跃,所以有活泼泼的自然界,乃是因为良知流行,良知发用流行于芸芸众生的世界,才能焕发它的生机,故致良知也是修行工夫。其二是辨别善恶。在王阳明心学中,良知是万物的准则,“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这个准则加以确立和落实,以为判断是非善恶的绝对标准。阳明说:“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这就是说,意念接触事物之处会出现是非善恶,由于意念与良知一体,所以良知能辨别是非善恶,这就是致良知。阳明说:“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覆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所谓“致其良知之所知”,就是依良知所知为善去恶,否则就是昧着良知。这样,“致良知”不仅是发挥良知明觉精察的功能,而且必须具体落实。同时,“致良知”辨识功能是无时不在的,阳明说:“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若必待疟发而后服药调理,则既晚矣。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良知明洁如镜,无丝毫的纤尘沾染,美丑往来,自然呈现,但没有任何踪迹留存;因而“致良知”工夫不分有事无事,时时刻刻都坚守岗位而勤勤恳恳地发挥其辨识功能。其三是去除私意。良知是至善,是道义、公正的象征,因而良知的存在,便意味着去除私意,但要将良知的去私功能发挥出来,必须“致良知”。阳明说:“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清,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清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温清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清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温清之物格,然后知温清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温清之良知,而后温清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在王阳明看来,如果温清、奉养只是意念,那就不能认为是“诚意”,也就是还不算真正的温清奉养。只有践行温清奉养,且不杂私、不自欺,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温清奉养,不是为了做给人看而温清奉养;知晓温清奉养之节之宜,是所谓“知”,还不是“致知”,“致知”是明白何为温清之节之知而实行温清,明白何为奉养之节之知而进行奉养,也就是“行”。温清奉养只是“物”,还不是“格物”,只有按照良知所知当如何为温清之节而为,彻彻底底,无一毫之不尽,只有按照良知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而为,彻彻底底,无一毫之不尽,此才叫“格物”。如此,温清奉养便真正得到了落实,也就是“致良知”了。可见,对王阳明而言,真正的温清奉养必须是“念头干净的”“过程完美的”“彻底贯注良知的”,即只有将良知贯注于温清奉养之中,而良知即天理、道心,也即无私意,阳明说:“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因此,“致良知”必然是去私意的。
3.致良知的实践向度。所谓“致良知”的实践向度,即从实践意义上认识“致良知”的内涵。就实践向度看,“致良知”约有三方面的意涵。其一是见诸行为。虽然良知是善体,是所有善的凝集,但仍然是以观念形式存于心,故必须诉诸实践。因此,“致良知”不能停留于言说,必须见诸行为,将良知落实到生活实践中,从而对生命、生活施加积极影响。阳明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天地间呈现的活泼泼世界,便是良知的流行不已,因而致良知即“必有事”,所以,“理”或良知不仅是不可离,实际上是无法离。“必有事焉”出自孟子,强调从实际的事为上修身养性,培养浩然之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歇,也不能刻意勉强,要顺其自然。即说,人应该时刻保持内心的充实和活力,不断通过内心的良知去指导、激励自己的行为,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能坚守本心,不为外物所动。这是强调通过实践行为来培养德行、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性。那么,“必有事”的具体情形如何呢?阳明说:“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致知在于格物,格物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便是根据良知所知之恶而去之、根据良知所知之善而为之,如此“致良知”便实而不空。关于“致良知”之实践品质,王阳明还以“舜之不告而娶”与“武王不葬而兴师”为例来说明。阳明说:“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如果仅从经典上找根据,那么舜、武王所为都是错误的,但如果从舜“诚于为无后”的实际情形、武王“诚于为救民”的实际情形看,则必然肯定舜、武王的行为,这才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必须在实事上做工夫,不能停留于空虚之论上。其二是物得其理。良知是善体,是天理,是准则,其功能有监督、照察、去污等,也是万物的尺度,因而必须将良知的内涵与功能体现在事事物物之中。阳明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弗自得也矣。”所谓良知即“是非之心”,即谓良知是是非的根据或标准,这种标准或尺度是先天的,人人皆有,但必须贯注于事为,才能成为天下“通达之道”。既然只有将良知推至事事物物,才能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从而确立事物之“理”,那就必须努力将良知推行至事物中。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将“心”中的良知推向事物,就是让良知在生活中得到体现,使良知对象化,“理”或良知见诸事事物物。通过“致良知”使良知或天理体现在事物之中,也就是用良知“控制”或“妆点”事物,从而使事物各得其“理”或良知,从而将事物或实践价值化而得到规范、引导和升华,此即“合心理为一”,也就是“致良知”。可见,使良知成为事物之理从而建立法则,是“致良知”的重要内容。其三是推扩善体。王阳明认为,仁或良知是造化不已的源头,他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人皆有仁心,皆有良知。这个仁心或良知好比冬至,虽然只有一阳,但这个阳是种子,是希望所在,通过持续努力扩展,最终拓展为六阳;亦如树木,必须有根,而后才能发芽、长枝、生叶。而良知的根是孝,因而必须由孝推及悌、推及忠,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就是“致良知”。阳明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有一个,事亲的良知与从兄的良知、事君的良知是同一德性,都是真诚恻怛,都是仁;但事亲的良知是本原,从兄的良知、事君的良知都源于事亲的良知;因此,只有将事亲的良知(孝)加以扩充,才能实现从兄的良知(悌)和事君的良知(忠)。如此,茫茫宇宙便洋溢着良知之爱、芸芸众生便传递着良知之善。此即善体的扩充,亦即“致良知”。
可见,“致良知”表现为多重内容,种植善根、积蓄善德、中和自然属于“致良知”的本体层次,自省修为、辨别善恶、去除私意属于“致良知”的工夫层次,见诸行为、物得其理、推扩善体则属于“致良知”的实践层次。这就是说,“致良知”首先必须有“良知”,其次必须掌握“良知”,最后将“良知”付诸实践,从而提升生活与完善生命,因而“致良知”是一种具有内在结构的生命自善的有机系统。这就是“致良知”的内容所在。
二、致良知条件的多样性
诚如上述,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目标,但致良知并非易事,王阳明对此有深切且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倡导致良知、鼓励人们致良知的同时,不仅对致良知的条件提出了要求,而且对致良知可能遭遇的困难也给予了警示。牟宗三认为,“致良知”并无什么巧妙方法,只有“逆觉体证”,他说:“本质的工夫唯在逆觉体证,所依靠的本质的根据唯在良知本身之力量。”“致良知”无疑要建立在“良知”力量本身,也必须“逆觉体证”,但如何“逆觉体证”却仍需配套工夫。杨国荣则说:“良知尽管具有先天的性质,但致良知作为一个过程,却无法完全离开后天的经验活动与理性活动。”所谓“经验活动与理性活动”,也就是“致良知”的条件。那么“致良知”究竟需要配备哪些条件呢?
其一是必须不断成熟。这是“致良知”的基础要求。孟子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仁德好比五谷,需要不断走向成熟才行,即指仁德需要修炼至熟方显光芒。王阳明继承了这一观念,认为致良知也必须修炼至熟,他说:“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傍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根据王阳明的判断,学生聂文蔚之德尚未完全莹彻,乃是因为致良知尚欠火候,如果致良知达到了火候而至纯熟,那么其品德便可谓莹彻。王阳明还以在大道上赶车为例,认为聂文蔚已然在康庄大道上骑走,之所以出现横斜迂曲,乃是因为聂文蔚所骑骏马尚未调教完备。因此,致良知如要达到仁德莹彻之层级,就必须使工夫成熟,从而达到至纯之境界。因而在回答弟子欧阳崇一“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的问题时,道:“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因此,致良知是工夫持续成熟的过程,诚如韦政通说:“致良知却是由次第、积累的工夫而得。”非虚言也。
其二是必须无私意掺杂。这是“致良知”的性质要求。致良知是推行善、落实善,这种“造善”行为是不能掺杂一毫私意的,否则,便是对致良知的彻底否定。阳明说:“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因为致良知是每个人的自我修行,或者生命的自我完善,因而并不需要额外的培养,而如果有成败利钝、爱憎取舍之念掺于其中,如果有明确的私意掺于其中,那就是将致良知分为内外两事,这就是不诚不一,是私意。而掺杂了私意的致良知,必导致致良知彻底变味,而不能算是致良知了。阳明说:“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自不安。凡认贼作子者,缘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体认,所谓‘虽不中,不远矣’。”如果放弃富贵却另有所图,如果孝敬父亲、敬爱兄长也是目的驱使,那么这种致良知就不算致良知。温清奉养之事,也是如此,如果温清奉养,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为了谋取某种利益,那么这种温亲奉养也不是致良知。阳明说:“温清之物格,然后知温清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不仅要实际地温清奉养,而且要无私意地温清奉养,此乃真致良知也。
其三是必须持续专一。这是“致良知”的品质要求。孟子曾经批评那种在存善方面缺乏恒心的行为,强调“养夜气”必须持续不懈。王阳明继承了这种观念。阳明说:“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川水流动不息方显生机活泼,天地生生不已才彰春意盎然,致良知不能朝三暮四、半途而废,必须夜以继日、持续如一,这是心学的最高境界。因此,必须日日扩充良知,阳明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学习者应该根据每日觉悟良知的情形,有针对性地加以扩充,日复一日地扩充,直至无一丝遗漏,这样才算精一功夫,也才算真正致良知。钱穆说:“良知是一个能生长的东西,致良知的工夫天天用得勤,这知行合一的良知本体便也天天生长,天天完成。”此言亦不虚也。
其四是必须因人而异。这是“致良知”的机动性要求。孔子弟子三千,但每个弟子天分不同,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学之者,有困而不学者,因而必须因材施教。王阳明认为,良知虽然人人皆有,但致良知却因主体素质的不同而有异。他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圣人之学的目标就是致良知,但致良知因主体的差异而分三种形式:一种是自然而致者,这种形式属于圣人;第二种是勉力而致者,这种形式是贤人;第三种是自蔽自昧不肯致者,这种形式属于愚不肖者。由于良知人人皆有,因而头脑愚昧且品质鄙劣之人只要肯致良知,也能成为圣人。因此,致良知务必根据不同对象而进行,不同慧根的人应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阳明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每个人天分不同,致良知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展开;而且,每个人的良知觉悟天天都在提升,因而又必须根据良知觉悟提升的情况致良知。既然贤人、愚不肖者只要肯致良知,也能成为圣人,这就将良知学开放而平民化,否定了致良知对人群的限制,而为所有人追求理想人格奠定了思想基础;既然致良知需要根据主体的条件进行才有效,这就意味着致良知必须因人而异。
其五是必须适可而行。这是“致良知”的契合性要求。致良知虽然是心学大头脑,但面对具体的问题也必须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王阳明认为,良知源于心之自然,如果刻意而为,非良知也。不刻意、不勉强致良知,才是真正的致良知,是出于本心的致良知。阳明说:“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什么是致良知?“宜”是适合、舒适、开心,因而“心得其宜”,即心感到舒适、舒畅。如何才算心感到舒适、舒畅?就是在日常应酬中做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从而求得自足。因此,君子应该安于自己的身份去做与身份相应的事,而想法不应该超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但凡强求自己做能力所不及的事、勉强自己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能算是致良知。而只有“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才能使致良知得以实现,即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才能致良知。既然致良知需要适合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既然致良知需要以自己的能力和智力为前提,那也就是告诉人们,致良知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强大自己的能力,而不能随意僭越,更不能盲目践行。
不难看出,对王阳明而言,致良知虽然是成圣的唯一路径、根本大法,但并非随意、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修炼成熟,从而排除半生不熟,即致良知工夫必须达到特定火候;它需要公正道义,从而排除私心杂念,即致良知工夫必须廓然大公;它要求持续专一,从而排除朝三暮四,即致良知工夫必须聚精会神;它需要因人施教,从而排除忽略差异,即致良知工夫必须有针对性;它需要适可而行,从而排除盲目作为,即致良知工夫必须量身而行。概言之,致良知如要顺利展开且必最终完美地实现其所有效应,就必须具备这些条件。
三、致良知效应的多向性
效应是指在特定环境下,由某种原因和结果构成的一种因果现象。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即“扩充仁义礼智与保四海”构成了扩充“四端”的效应。所谓“致良知效应”就是指由“致良知”与其所导致的结果构成的因果现象。诚如上述,“致良知”是心学的根本大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是将“心之本体良知”推及生活实践,因而“致良知”必然产生广泛效应。那么,“致良知”究竟会产生哪些效应呢?
1.表现为最高智慧的效应。在阳明心学中,致良知是最高智慧,所谓“良知之外别无知”,那么作为最高智慧的致良知表现出怎样的效应呢?其一是足以应对千变万化之事象。儒家思想中有一个特殊观念,就是认为具备了至善之德,即所谓最高智慧,其他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中庸》第三十二章)为什么“至诚”能够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因为至诚是“天德”,君子做到了“至诚”,所以“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中庸》第十二章)。王阳明似乎继承了这种观念,认为“致良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应付所有情况。阳明说:“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这就是说,只要致良知,世上千变万化之事,都能应对,所谓不可穷究之秘,也尽在掌握之中。致良知也可以帮助人们把握千经万典的核心、认识异端曲学的本质,只要加以权衡比较,便清晰可见,没有能逃离者。阳明说:“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至于“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则完全与致良知相悖。概言之,无论大事小事,无论难事易事,无论千变万化,只要致良知,便能应付自如,便能迎刃而解。其二是足以成就圣人。成圣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本目标,但成为圣人的基本资格是立德,即拥有高尚的道德品德。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尽心下》)圣人是百代之师,伯夷的人格贞操,贪腐者闻之而为清廉,懦弱者闻之而为刚强,柳下惠的贞操,刻薄者闻之而为纯厚,狭隘者闻之而为宽阔。但在王阳明这里,拥有高尚道德之前提是“致良知”。阳明说:“夫学者既立有必为圣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觉处朴实头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无许多门面折数也。”如果学者立下了成为圣人的志向,只要根据自己良知觉悟之处做去即可以成为圣人了,所谓“良知觉悟之处”,就是良知确认之事件、之行为,良知是至善,是美德,是天理,所以按照良知觉悟之处去做,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如果不能致良知,非但不能成为圣人,反而陷于小人之地。阳明说:“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入于小人之归。”即便人之不善达到逆理乱常之极点,良知也能了如指掌。但如果不能致良知,则物不能格、意不能诚,从而陷于小人之道,而与圣人越来越远矣。其三是足以化腐朽为神奇。致良知也可使愚昧转为聪明、使丑陋转为美丽,并决定德行的性质。一般情况下,老实被视为一种美德,但王阳明认为,老实只有贯注良知才能成为美德,如果老实只是一种用于获得利益的花招或智巧,那么这种老实便是虚伪了。阳明说:“谓之老实,须是实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谓老实者,正是老实不好也。昔人亦有为手足之情受污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于良知亦自有不安。”就是说,如果老实中没有良知,那么这种老实是不可取的。致良知也能使愚笨之人变聪明。阳明说:“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昏昧之人如果能就事物精察其“理”,以唤醒、坚守良知,那么他必定转为聪明。致良知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贡献处世的方法、决定事件的性质,阳明说:“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矣。”就是说,如果顺良知而为,那就好比心中有了灯塔,可以提示你如何应对。比如,如果良知在心,即便不量脚的大小就去编草鞋,也不至于编成筐子。可见,致良知不仅能主宰德行的性质、不仅能转愚为智,而且是做事的大头脑,使中正不偏,所以说“致良知”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阳明说:“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虽千魔万怪,眩瞀变幻于前,自当触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阳一出,而鬼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尚何疑虑之有,而何异同之足惑乎!”即便“千魔万怪”,触良知而碎;鬼魅魍魉,遇良知而遁形。如此良知尚不神奇乎?
2.表现为推扩善德的效应。在阳明心学中,致良知便是推扩善德,那么作为推扩善德的致良知表现为怎样的效应呢?其一是足以推行仁德。在王阳明心学中,良知就是仁,就是明德,就是天理,就是至善,而“仁”是万物一体的基础,所以良知是万物一体的基础。因此,如果说推行万物一体之仁有另一形式,那便是“致良知”。早期儒家有“亲亲人民爱物”之说,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教,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告诉我们,仁义礼智“四德”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如火之使然、泉之始达,才能保四海。王阳明“致良知”继承了这种推爱方式,他说:“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只有致力于推行良知、实践良知,才能公正地判断是非、客观地统一好恶,并能视人如己、视国如家,从而实现万物一体之仁。阳明说:“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只要致良知,那么从爱吾父到爱人父,再到爱天下之父,就是孝德的实现,从爱吾兄到爱人兄,再到爱天下之兄,就是悌德的实现,其他君惠臣忠、夫义妇顺、朋友之信等,以此类推,直至家齐国治天下平。可见,“致良知”便意味着万物一体之仁的全面实现。“致良知”之推扩善德还可以提升人的道德素养,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致良知能够使人公正是非、一同好恶、视人如己、视国如家,不仅能获得全体人民信任,而且可让全体人民喜悦。其二是足以治疗负面之心态。人的心态不仅千奇百怪,而且千变万化,其中有些属于消极有害心态,所以需要滋养或治疗。骄傲是儒家非常厌恶的一种负面心态,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是优异品质的象征,小人是拙劣品质的象征,因而言小人傲慢无礼而不坦然,自然是对傲慢心态的批评。王阳明甚至认为骄傲是天下最大的恶,他说:“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那有什么药方治疗傲慢之心呢?只有致良知,阳明说:“但知得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认识傲慢所在,便是良知;对傲慢的去除,便是致良知,也是格物。因此,人心本来廓然大公,没有私欲窒塞,没有私欲障碍,展示的是广袤无边、风平浪静的心态。但如果被障碍、被窒塞,表现为傲慢等消极心态,就必须致良知,以良知化解窒塞和私欲。阳明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面对嘲讽和毁谤,不受任何影响而能保持平和心态,只要坚持致良知便可以做到。阳明说:“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出自《易传》,大致意思是,隐遁世间而不感到苦闷,不被世人认同也不感到苦闷,所以是一种超脱之心态。有了这种超脱心态,面对嘲笑、毁谤、荣辱等都能付之一笑。而拥有超脱之心态,必须遵循良知而为,以良知融于心而至于中和。其三是足以抵御色利的诱惑。良知是至善本体,代表道义、正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钱财与地位、功名与利禄都是人想要的,但必须通过道义手段获得。这也是儒家对于功名色利的基本主张。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以道义手段获得,那就必须拒绝财富、地位、色利,即不能被功名色利所诱惑,不能因毁誉得失而俯仰。“致良知”也具有这种效应,阳明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但凡事物往来,只以良知应付就足够了,那些沉湎虚名私利之人,那些斤斤计较毁誉得失之人,都是未能真正致良知。因此,如果纠结于毁誉得失、沉湎于声色名利,只会残害良知。事实上,意念处是否“善”,良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真能致良知,那么财富地位、功名色利、毁誉得失等,都不能成为诱惑而使人陷于不义之地。这就是说,“致良知”是以其内含的道义、公正抵御、化解功名色利、财富地位、毁誉得失的影响。
3.表现为容受知识的效应。“致良知”的大门对于科学知识是关闭的,还是开放的?这是学界聚讼不已的问题。我们先考察王阳明的相关论述。阳明说:“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圣人之学何以至易至简?因为圣人之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恢复心之本体,而不是知识技能之类。这句话含有“知识技能”无助于人恢复心之本体之意,所以实际上已将“知识技能”独立于圣人之学。阳明又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既然“致良知”不属于“扩充知识”的活动,那么事物之理的知识当然不在“良知”范围,因而“致良知”不可能将“扩充知识”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迥异的观点,代表人物分别是牟宗三和劳思光。牟宗三说:“良知天理决定行为之当作,致良知则是由意志律而实现此行为。然在‘致’字上,亦复当有知识所知之事物律以实现此行为。吾人可曰:意志律是此行为之形式因,事物律则是其材质因。依是,就在‘致’字上,吾人不单有天理之贯彻以正当此行为,且即于此而透露出一‘物理’以实现此行为(实现不只靠物理,而物理却也是实现之一具)。是以在致字上,吾人可摄进知识而融于致良知之教义中。要致良知,此‘致’字迫使吾人吸收知识。一切活动皆行为。依是,致良知乃是超越之一套,乃是笼罩者。在此笼罩而超越之一套中,知识是其中一分。就此全套言,皆系于良知之天理,犹网之系于纲。从此言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然而此全套中单单那一分却是全套之出气筒,却是一个通孔。由此而可以通于外。在此而有内外之别,心理之二。此个通孔是不可少的。没有它,吾人不能完成吾人之行为,不能达致良知之天理于阳明所说之事事物物上而正之。是以此知识之一外乃所以成就行为宇宙之统于内。”在牟宗三看来,第一,“致良知”是由意志律实现的行为,所以“致”字上当有知识所知事物律以实现此行为;第二,“天理”的贯彻,必须有物理事理的助力,否则是空寂;第三,因而需要摄进知识而融于良知之教义中;第四,只有摄入“知识”,心学或致良知方获得一个“通孔”而有活力,从而与宇宙连成一片。此也就是所谓“良知坎陷”。这就是说,“致良知”在义理上是不排斥知识的,而且必须接纳知识才不会窒息。牟宗三说:“良知既只是一个天心灵明,所以到致良知时,知识便必须含其中。知识是良知之贯彻中逼出来的。否则,无通气处,便要窒死。”不过与牟宗三不同,劳思光则明确断定良知学是排斥知识的。首先,“良知”属于道德语言,劳思光说:“盖阳明用‘良知’一词,原指价值意识及作价值判断之能力而言,属于‘道德语言’而非‘认知语言’。依阳明自己之解释,即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被界定为‘知善知恶’之能力,分明与认知事物或规律之‘知’,截然两事。而所谓‘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正表明阳明心目中并无认知意义之‘知’也。”其次,既然“良知”只是“知善知恶”的能力,那就不属于认知事物规律之“知”。劳思光说:“阳明用‘知’字与通常谈认知活动者用‘知’字不同。盖阳明只就‘良知’之义说‘知’,并不论及独立于道德意识之纯粹认知也。”因此,知识从未成为“致良知”的任务,劳思光说:“合而观之,阳明对‘知识问题’之态度,可说乃一消极态度;盖阳明只承认道德行为之价值,而不认为独立意义之知识活动有何独立价值。对事物之理之知识,只在能有助于道德行为之完成时,方值得注意;因此,认知活动内部之种种问题,亦更不在阳明探索之范围中。”但劳思光认识到,即便是“致良知”这种纯粹的成德工夫,仍然需要有对知识的关切,或需要知识的支援。他说:“但由于人之道德行为必涉及具体之世界,因而必有具体之内容,故在论及道德行为之内容时,仍不能不对事理之认知取一确定态度。”事实上,牟宗三与劳思光关于“致良知”的异趣解释,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人面对西方哲学的复杂心理。牟宗三的解释,以放弃“良知”的尊严为代价,也就是为了迎合“知识”这种新奇之物,而充分发挥义理上的诠释空间;而劳思光似乎更能忠诚地对待心学,没有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转而要求“致良知”卑躬屈膝、自我投降、擅自增损。更言之,如果立足于王阳明自己的立场,那么“致良知”应该不属于“知识”范畴,也就是“致良知”的推行,不能带来扩充知识的效应。而这或许又是牟宗三之解释得到肯定的原因,因为牟宗三的解释的确为“致良知”敲开了一个道孔,从而激活、扩展了“致良知”的生命。而王阳明关于良知可以使人之器官顺利发挥功能的认识,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致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阳明说:“盖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又何有于聪?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又何有于睿知?然则又何有于宽裕温柔乎?又何有于发强刚毅乎?又何有于斋庄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乎?”这就是说,耳所以能听,目所以能视,心所以能思与觉,进而表现的聪敏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斋庄中正、文理密察等,皆得益于致良知,即谓致良知可以改变感官的效果与性质,从而显示了致良知并非天生拒绝知识。
总之,致良知的效应,不仅能应对千变万化之事象,不仅能助人实现成为圣贤的理想,而且能化腐朽为神奇;不仅能推行万物一体之仁,不仅能治疗人之消极心态,而且能抵御声色利欲之诱惑;而对于“知识”并非本体上的拒绝,只是功能上的防御;可见,“致良知”效应几乎涉及人伦世界的所有范围。因此,如果将“致良知”的效应做个扼要的归纳,那就是“确定万物的秩序,孕育万类的生长”——“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弗自得也矣。”因而即便陷于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之地,亦不会受影响而自得其意。这,岂不是王阳明致力于良知学的建构、普及之初衷?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