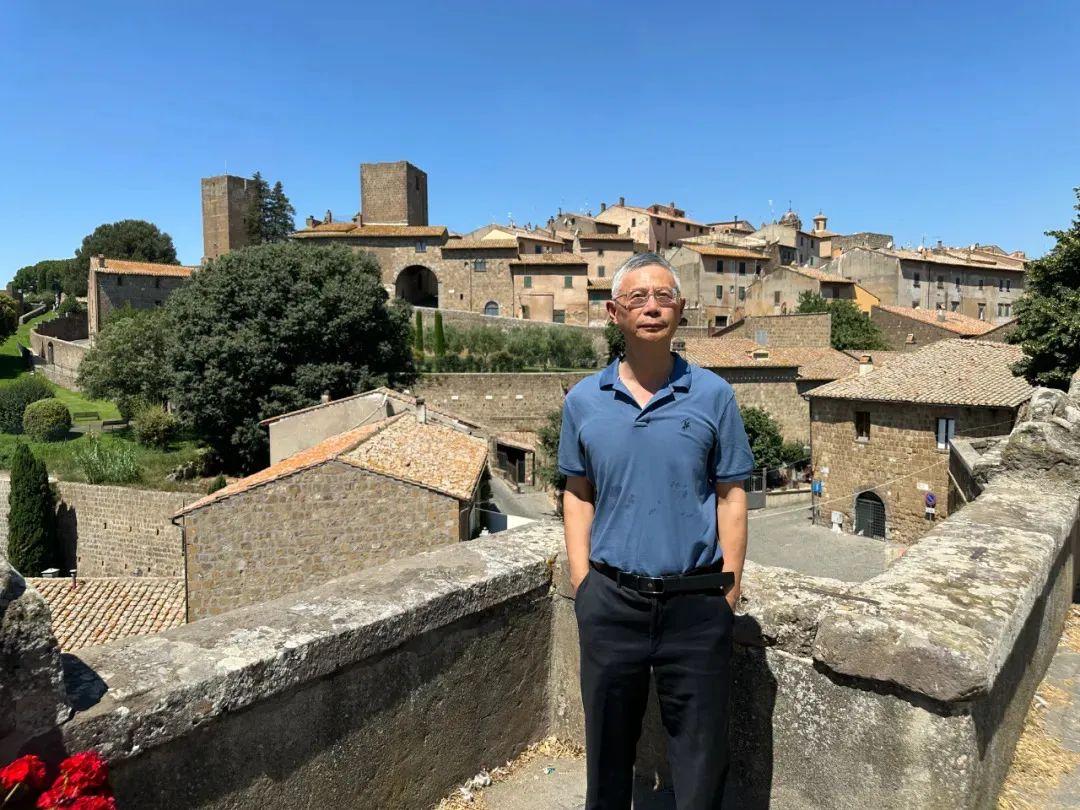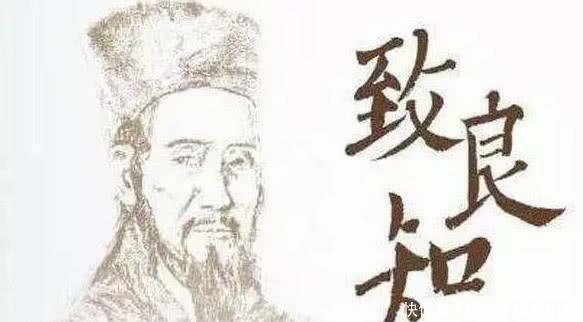【作者简介】陈春芳,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船山学与宋明理学。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规范伦理学视域下的朱子学研究及其现代转化”(项目编号:FJ2022C09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朱子‘诚意’思想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720221038)。
原刊于《朱子学研究》编委会编:《朱子学研究》第43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
【摘 要】 王门弟子季本曾对“诚意”之学多有阐发,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信息。在批判朱子“诚意”说的基础上,季本接续了其师的理论进路,进一步从心学脉络对“诚意”文本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在季本看来,朱子以“实”训“诚”具有造成天道与人道二分的倾向,“诚”应当以“成”训之,乃个人“自成”之意,这实质上是将人道归纵于天道,个人成为天命流行中的必要一环。对“意”而言,季本将其定义为“天命流行之几”,“诚意”工夫也就是“成就此天命流行之几”,从而与天命流行相接轨。在“诚意”工夫中,“谨独”作为“诚意之要”,强调在体上用功,以恢复天命本体精纯贞一的状态。总体来说,朱子的“诚意”思想体现出天道与人道分殊统一的理学架构,季本的“诚意”思想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纵贯为一的心学架构,这背后所揭示出的义理脉络,使得“诚意”构成了观察理学转向心学的研究新视点。
【关键词】 季本;朱子;诚意;谨独
导 言
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朱陆异同、朱王之争常常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议题,这其中涉及如何理解理学向心学的转变。对此,学界多从“心与理为一或为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等框架去理解这场思想史转变,而这些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格物”为视点的。就 “心与理为一或二”而言,朱子本人也讲“心与理一”、“心之为物,众理具足”,并且将其作为学问的基石:“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但后人却以朱子主张向外“格物致知”以去除气禀物欲之蔽而将朱子心、理关系简单理解为“心与理二”,而忽视了朱子与陆九渊在哲学上的相通之处,即“心与理一”。可见,这一基于“格物”的视点易将无差异之处差异化,进而忽视了真正的差异,并不能准确把握理学与心学的整体脉络与义理内容。同样,以“尊德性—道问学”来诠释理学与心学之异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基于“格物”的视点,朱子工夫论就显得偏向于“道问学”,即通过后天的学习活动获得对外在之理的认识;陆象山则偏于“尊德性”,即更为突出德主体的先验意识。严格说来,“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区别仅代表朱陆在鹅湖之会时的分歧,但以“格物”为视点就有将此扩大化至整个理学与心学分别(包括朱子与王阳明的分歧)的倾向与嫌疑。
质言之,“格物”视点主要侧重于考察“知性”与“德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基于“格物”视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自觉地将“知性”与“德性”的区分等同于理学与心学的区分,而这不论对于理学还是心学的理解而言都是片面的。对此,本文试图发展“诚意”这一新的观察视点,将理学与心学都放置在“德性挺立”这一视域下进行探究。郑泽绵认为“‘诚意’问题才是促进朱子与王阳明思想发展的真正核心”,是理学转向心学的内在视角。本文将延续郑泽绵的思路,并进一步将这一观点推进至理学与心学在义理架构层面的分析。在这方面,王门弟子季本成了良好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季本在弘扬师说的同时,其独特之处在于以参经注疏的方式去理解阳明,这使得心学思想有了系统的经学依托;另一方面,季本的相关著作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批判,由此阐发了颇具个人特色的“诚意”思想,其中涉及理学与心学在义理架构层面的分歧。因此,本文以下将以诠析季本的“诚意”思想为主体,并借此深化观察理学向心学转变的“诚意”视点。
一、诚
理学与心学对“诚”有不同的训释,其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理论进路。朱子将“诚”训为“实”,意为“真实无妄”,分别指向“理”与“心”,即诚“有实理而言”,又“有实心而言”。但在季本看来,“理”与“心”乃是“一体之变化”,朱子以“实”训“诚”具有造成天道与人道二分的倾向。因此,季本以成”解“诚”,将人道作为天道流行中的必要一环,体现出与理学不同的纵贯架构。
(一)诚之为言成也
《四书私存》有言:
诚之为言成也,本于成之者性而言。朱子以实训诚,实不足以喻之。盖实者有物在中之名,而诚则不倚于物者也。诚者,天之道也,实理流行,无所勉强,乃天命之本体,惕然不能自已,所谓微之显而不可掩者也。
在季本看来,朱子“以实训诚”抹杀了“诚”的独立性。“实”作为“有物在中之名”,偏向于物理空间概念,更多指的是一物占据另一物的虚空之处,这也就意味着“实”的概念必须借助于外物才能够成立,因而季本认为“实”不足以尽“诚”之意。在他看来,“诚”乃“天之道也”,是不依赖于外物的实理流行,若以“实”训“诚”将会使其因依赖外物而丧失独立性。因此他主张“诚之为言成也”,“成”乃“成就”之意,个人通过“自成”的工夫就可达于“诚”,无须依赖外物。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自成”的工夫乃是天命本体的惕然流行,在此人与天道一以贯之,呈现出直下纵贯的义理架构。
季本进一步言:
诚以成而得名,盖本于“成之者性也”。凡天下之物,其能成者皆诚也。诚者自成,以心而言,自成即其成己也。人虽曲成万物而不遗,不过以此诚心自诚己而已。诚之理散于万事者即是道也,以此道应万事,则自明而诚,归于诚之本体矣。
对“诚”之本体义,季本同朱子一样都将“诚”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但关于“诚”落实在人道处的看法却迥然有异。在季本看来,《中庸》的“诚者自成”与“道自道”都是在心层面而言,“诚者自成”指的是个人通过“自成”的工夫达于诚之本体,因此,“自成”即“成己”。季本将“诚”收摄于内心,万事万物不过是以此“诚心自成己”而已。同样“自道”也是如此,“自道者由己而不由人之意,即所以自成也。”,“自成”也就是“自道”,都依赖于主体个人的工夫。季本将“自诚”与“自道”放置在心层面,与朱子将“诚”二分为“理”层面与“心”层面有着本质的不同。朱子在注解“诚者自成”与“道自道”时,言“上句工夫在‘诚’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诚”指的是“是个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强调“诚”的自然义,此时无需人为工夫的参与。而“行”指的是“道却是个无情底道理,却须是人自去行始得”,强调人为工夫的参与。相较于朱子将“自成”与“自道”分别作为独立运行与人为参与的产物,季本将“自成”与“自道”融为一体更凸显出心学特征,这一点在“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注解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诚字皆以心言,而朱子以“物之终始”泛言在天之实理,则不诚无物不可以实理言。
因曰在天本无不实之理,而在人或有不实之心,则两诚字遂分属天人矣。又言:“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殊不知物之所尽者,气也,若理岂有尽时邪?
《中庸章句》中,朱子异解第二十五章“诚者,物之终始”与“不诚无物”中的两个“诚”字。前者在天道处言“理”,是万事万物存在的依据,正如朱子所言:“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后者在人道处言“心”,指的是“人心或有不实”,而“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在季本看来,朱子既在“理”上言“诚”,又在“心”上言“诚”,实质上是将“诚”分属于天道与人道,这是季本所不能同意的。此外,对于朱子“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的注解,季本认为物尽只是气尽,并不是理尽,理是没有穷尽的,因此朱子从“理”上言“诚者,物之终始”是说不通的。这里季本通过对朱注的批判阐扬了自己的观点——“诚字皆以心言”。“物之终始”“不诚无物”都指向了心体的流向与运作过程。相较而言,朱子分别从“理”上与“心”上言“诚”的确有割裂天道与人道之嫌,而季本以“心”解“诚”更凸显出纵贯特征。
(二)成己即成物
理学与心学对“物”分别有着不同的理解。朱子言“物”既泛言客观之万物,又专言人之所对物;而季本言“物”则仅指与人之所对物,从而将物收摄于心。季本有言:
物者,己之所自成,但于事处之各当,以正性命,便是曲成万物,岂在外物上求成哉?
成物即是成己之见于处物者,即所谓道也。但自人化而验其成耳,道外岂有物哉?
季本认为,“成物”就是“成己”,“成己”便是“成物”,“成己所以为成物,以成物之道,不外于成己也”。由“成己”到“成物”是自然而然的心体的落实,乃一体之工夫,并非如朱子所言“必先成己,然后能成物”,“成己”与“成物”乃是有先后次序之分的两截工夫。朱子与季本对“成己”“成物”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源自对“物”的不同理解:
至其言物,则亦有不同者。如曰“诚者物之所以自成”,则本程子“至诚事亲,则成人子;至诚事君,则成人臣”之说也。盖事亲而自成者,子也;事君而自成者,臣也,是以臣、子之身为物。及注成物,则云:“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行于彼”,是又以成物说向外去,两“物”字不相应矣。何则?臣、子之身属自己,则己之所对,方始是物。如子是己,而所对者父是物;臣是己,而所对者君是物,则物不可以言己矣。
在季本看来,朱子“诚者自成”的注解(“诚者物之所以自成”)是本于程子“如至诚事亲则成人子,至诚事君则成人臣”的说法,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是以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子”与“人臣”为物。但在对“成己”与“成物”的注解中,朱子以与主体相对的客体言物,而这两个“物”概念是不一致的。在季本的分析中,朱子的诠释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不一致,根本上是因为以主体自身言“物”曲解了“物”的概念,“物”只能在与主体相对的架构中才能成立,即所谓的“己之所对,方始是物”。实际上,季本对朱子的批判有失公允,朱子之所以有不一致的“物”概念,恰恰是因为在朱子的理学架构下,“物”既可专指人之所对物,又可超越主客对待而泛指万物。在对“不诚无物”的诠释中,朱子曾言:“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唤做物。”此时“物”在“眼前”,与“己”相对,处于与人相对的结构中,但在“诚者物之终始”的诠释中,朱子言:“‘诚者物之终始’……物,事也,亦是万物。”此时“物”可以超越主客对待地泛指万物。由此可知,理学与心学视阈下的“物”观是不一致的,而造成这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理学与心学不同的理论架构。理学泛言客观之万物,指的是在天理落实为万物的过程中可以没有人的参与,天道直接化生万物,强调的是“理”超越主客对待的实在性;而专言人之所对物,指的是在天理落实为万物的过程中有了人的参与,天道落实为人,强调的是人道对天道的赞助。但在心学看来,“物”必须纳入人的意识结构中,或者说人的照看之下,其实质强调的是在天道(良知)落实为万物的过程中,人的活动扮演了必要的环节,即天道(良知)的落实离不开人道的运化,同时万物的生成也离不开人道的照看。
二、意
季本以“成”释“诚”,将人道纵贯于天道,又对“意”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认为“意”乃“天命流行之几”。据此,诚意工夫便是成就此“天命流行之几”,这意味着诚意工夫与天命流行相接轨。可以说,季本通过对“诚意”的阐释将朱子理学的义理架构扭转至心学。
(一)意乃天命流行之几
季本对“意”定义为:
意者天命流行之几,即其惕不能已者,是己所以诚之,亦惟不自欺其本体之惕然耳。
以“天命流行之几”解释“意”,是季本相较于前人独具特色的阐释。结合对“诚”的解释,季本所言的“诚意”实际上就是主体对此天命流行之几的成就,即主体在本体层面警惕用力以防物欲利诱的侵扰,从而使天命按其本来状态发用流行,因而季本对此的另一说法是“不自欺其本体之惕然”。对于“几”,季本定义为“独知之处,从诚上发端,所谓几也”、“人心动时,最易放失,故为学之要莫切于几”。“几”乃是天命本体与外物相涉时最容易出现变化的关键环节。朱子说:“诚,性也;几,情也。”与朱子从“情”上说“几”不同,季本将“几”上提至天命本体层面:“诚、神、几,皆因天命本明之体而异名,诚是明之聚精处,几是明之不息处,神是明之往来不测也。”不论在周敦颐还是朱子那里,“几”都被理解为善恶的关口,所谓“诚无为、几善恶”,而季本所理解的“几”实际上指的是纯善本体(诚、天命本明之体)在经验世界的发端,其道德属性应当说是纯善的。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在于:季本将心体归纵于天命流行,因而原本作为人心理活动最易出现变动的关键环节的“几”便被提升至作为对天命本体发用流行之初的刻画,而这恰恰是朱子站在其理学立场上所不能认同的。
经由上述对“几”的分析,季本的“诚意”思想既不同于朱子,甚至也不同于阳明。在朱子的理论体系中,“意”乃是有善有恶的,因而朱子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而使此心获得此理,从而为“诚意”工夫提供一个判断意念善恶的根据。而在季本这里,作为具有纯善属性的“天命流行之几”,“意”是本体直接发用流行的最初状态,显然也是纯善的。这一点从季本对“意”的另一个创造性提法中亦可获得确证,季本说:“身心意知物皆明德本明之体,发于用而属动者也,动则其势不可遏矣,修正诚致格乃复其本体,静功也。”与朱子一样,季本亦将“明德”视为天命在人处的落实,因而将“明命”与“明德”联系起来,所谓“明命即明德,命之在心为德,德之不已曰命”。无论作为明德之本体,还是作为明德本体中的一环,“意”都被上提至本体层面,从而作为本体流行发用的某种纯善之物。在这个意义上,“诚意”工夫便不是以外在之理规范内心之意,而是人直接纵承此天命,成就其流行之几。可以说,季本正是通过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批判与新诠,将原本在“诚意”话语下显示出的“心—理”对待的理学架构扭转为天人纵贯的心学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也曾对朱子“诚意”思想中所显示出的理学架构进行了批判:“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正因觉察到朱子以外在之理规范内心之意的工夫进路存在一定的断裂,阳明主张直接以人本具的“良知”来对“意”进行监察判断,善意则扩之,恶意则克之,从而落实“诚意”工夫。阳明一改朱子的“诚意”诠释,将所有工夫都收摄于“良知”之下,主张一种将良知扩充至极而实行(致良知)的纵贯工夫。但阳明始终未将“意”视为“良知”的直接呈现,因而作为“心之所发”的“意”始终具有“有善有恶”的特征,这不免面临与朱子相似的割裂,即先验层面的纯善“良知”与经验层面的有善有恶之“意”之间的冲突与割裂。在这个意义上,季本在“诚意”工夫上比其师阳明走得更远,其话语背后更为鲜明地体现出心学的纵贯特征。
(二)诚意与自欺
处理“诚意”与“自欺”这一对立范畴之间的关系,是“诚意”思想建构的一大关键。季本在注解《大学》“诚意”章时言:
自欺者,天命本体之在我者不为主,至为外物所诱,不能胜而加掩焉者也,此正其知其有蔽处。毋者,意有所不安而不欲为也,毋自欺即是致知,但自其惕然动者而言,则曰诚意耳。自慊者,其意常安。无所不足也,毋自欺则自慊矣。
本将“自欺”解释为天命本体在人处主宰性的丧失,这种丧失使人不能免于外物的侵扰,而不得不在伪善的掩盖下做出违背天命的行为。在季本看来,对外物所诱的掩盖要以对外物所诱的觉知为前提,因而“自欺”显示出“知”的灵明,即能够知道外物所诱对人心所具有的消极的遮蔽,也就是“知其有蔽处”。因此,“毋自欺”便是调动并扩充此灵明之知而去除外物所诱的遮蔽,也就是“致知”。这样一来,“致知”与“诚意”便打并为同一个工夫,即在本体处的时刻警惕用力,而作为“意常安”的“自慊”则意味着本体流行无所不足的状态。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将“自欺”定义为“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在朱子这里,“自欺”乃是“心之所发”(意)与“知为善以去恶”之间的不一致(未实),而“知为善以去恶”与“格物致知”工夫的效验有关,正如朱子在论及“致知”时所说:“为善须十分知善知可好。”因此,“自欺”乃是基于“格物致知”而产生的道德心理学现象。朱子始终强调“格物致知”与“诚意”之间的“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这与季本将“致知”与“诚意”打并为一有较大的区别。进一步而言,这种区别实质上根源于朱子与季本学理架构的不同。相比于季本在其纵贯架构中将“自欺”理解为天命流行的阻碍,朱子将“自欺”理解为“知为善以去恶”与“心之所发”之间的不一致,更显示出其理论架构中所存在的某种横列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朱子的自欺观意味着人心灵存在的某种二元性,而这种二元性则进一步映射为理气二元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朱子言“知为善以去恶”,即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获得对理的把握,进而以此理对所发之意进行规范;另一方面,所发之意之所以具有流于恶的可能,根本在于气禀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的“自欺”观所表明的是“知为善以去恶”(理层面)这一对本体的认知与“心之所发”(意层面)这一经验性的状态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如果说季本所言的“诚意”工夫是恢复某种良知纵贯天人的本然状态,那么朱子所言的“诚意”工夫则更表现为以先天客观实存的本然之理规范捉摸不定的经验之心。
三、谨独
在“诚意”工夫中,季本尤为注重“谨独”,并且将“谨独”作为“诚意之要”,他说:“诚意之功只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要只在谨独。”对季本而言,“谨独”不仅是道德自修的手段,同时还因其与天命相结而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学问源头只在天命之性,尽性之学惟谨独而已。”
(一)“显”与“微”
对于“独”,朱子定义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这一说法同样为心学所继承,所不同的是心学将其理解为“本体之知”,指向心之本体层面。对于“独知”的诠释,季本始终围绕着“显”与“微”之间的问题意识:
圣人之道,不于用上求自然,而于体上做工夫。故虽至圣,犹孜孜舋舋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上做,不睹不闻,盖人所不知最微之处也。微则不为闻见所牵而反复入身,其入身者,即其本体之知也。故知为独知,独知处知谨,则天理中存,无有障碍,流行之势,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着于显处,以用言也。然非本于微,则所谓显者乃在闻见,而物失其则矣,不可以言道。
王学部分门人存有“主率性自然”的思想。季本认为过于强调心体的自然流露实则意味着工夫的落空,易产生认欲作理的弊病,因而主张在本体处谨惕自勉。在季本看来,于“用上求自然”是用工夫于“显”处,即声色闻见处;而于体上做工夫则是用工夫于“微”处,即“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处。有论者指出:季本的工夫具有归寂派色彩,即主张为学工夫是归于虚静之体的静功。因此,对季本而言,在工夫论上,将“显”归于“微”便变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季本指出,“微”处是不被见闻所牵累而入于深的内在状态,是本体之知,也就是“独知”。“独知”意味着“独”具有先天性的自我觉察能力,“独处必能知”。在这里,“独”被视为隐微之处的本体,并与天命相接,即所谓“天命本明之体也”,也是天理所存之处。一切用处显处的事物均由此发用流行。因而,如果说在“显”处的工夫易忽视微处的本体,那么归寂于“微”的静功则是抓住了根本。此“微”处的根本工夫便是“谨独”:
谨即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意,正所谓惕然也,独上何待于加谨邪?盖惧外邪之干己耳。
独知之所知,天命本明之体也。本明之体何所加慎于其上哉?其所慎者,惧外诱之为障蔽也。凡有障蔽,皆本体之知不明,失于照管故耳。此知常明,时时照管,则外诱之来,岂能障蔽?
季本主张于本体上做工夫,但本体自身圆满自足,又何须加工夫于其上?具体到“谨独”工夫来说便是在作为本体的“独”上何须加上一个作为工夫的“谨”字?季本认为,“谨独”只是在“独”的发用时预防外诱的干扰。“独”的发用只是“独”的自我觉知,因而避免外诱的干扰实际上也就是使作为本体之知的“独知”常明。与其师阳明一样,季本也反对朱子将“戒慎恐惧”与“谨独”分为两个工夫,而主张“谨独”就是“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处。在朱子那里,“戒慎恐惧”与“谨独” 分别是思虑未萌时的未发工夫与思虑将萌时的已发工夫,虽然朱子有时也将“戒慎恐惧”视为统体工夫。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朱子的这一区分将“谨独”仅视为在心之已发处对“意”的监察工夫。这对季本来说,这是在“显”处用功,即“在声色处着力”,因而有遗漏本体之嫌。
如果说朱子因强调工夫在次序上的先后关系而使得某些已发工夫有远离本体之嫌,那么季本将“谨独”与“戒慎恐惧”相等同实则是主张将一切工夫都归寂于本体,这的确显示出与聂双江、罗念庵等归寂派相似的理论进路。然而,季本的“谨独”工夫乃是本体的惕然而动,即本体流行当中便有惕然的呈现,“谨”便是“独”的流行、“独”的自我觉知,正所谓“独知之惕然知谨”。正是在这里,季本的“独知”工夫与归寂派又有所区别:如果说聂双江、罗念庵等人以“致虚守静”的工夫护住良知本体而不失,但工夫与良知呈现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季本实则肯定了惕然之谨的工夫便是“独知”(良知)的流行与呈现。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的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季彭山主龙惕不主自然,此皆为的使良知能保任守住而常呈现也。此本是常行,不影响阳明之义理。双江念庵之致虚守静……然经过此一关以体认寂体或良知真体,并不能一了百当,这不过是抽象地单显知体之自己,并不能表示其即能顺适地贯彻下来。”
(二)“独知”与“天命”
由上述分析可知,“显”莫不统于“微”,从而将万物都收摄于“独知”之内。这样一来,“独知”便构成了万物存在的根本,进而与天命流行相接轨。季本说:
君子必慎其独,独与上文自字相应,以我所自主而言,故曰独。本文不著知字,但独处必能知,故即以独知为独,此指天命源头不杂于物者而言也。
季本将“独知”等同于不杂于物的天命源头,而“独知”的呈现又依赖于个人自主性的工夫,这也就意味着季本将个人直接作为天命流行中的关键一环参与了万物化生。在季本的理论体系中,天命、独知、万物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存在:
昭昭者,天之显也。然言天者必曰“于穆”,穆则不显矣。盖显者,明之见于外也,自其藏于内者而言则谓之穆。以穆言昭,是显藏于不显也,在人则为独知,故至德亦惟不显而已。盖天之本体如此,故万物形形色色,往来不穷,即是天之感应处,而昭昭之体无所不在,物岂能累其明哉?
《中庸》有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又引《诗经》言:“为天之命,于穆不已。”在季本看来,“昭昭”是形容天之显,即天命流行而生成形形色色的万物,而“穆”是显见之天藏于内的本体。因此,形形色色的万物皆是天命“于穆不已”,是天之感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以穆言昭是将天命之发用内藏于不显的本体,而这一本体在人则为“独知”,亦为“至德”。可见,季本的“谨独”工夫不仅关乎个人道德的培养,同时还纵贯于天道流行,成为化身万物的存在根据,是一牟宗三意义上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系统。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独知”一词虽由朱子在注解经典文本时提出,但阳明与季本等心学家却基于对这一范畴的新释而扭转了其背后的理学架构。在朱子那里,“独知”本指人心对其意念萌动之初的觉察状态,并无本体意味。而接过这一概念的阳明却将其本体化,并与良知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原本仍需依赖格物致知才能实现对意念的规范的谨独工夫便被扭转为“独知”自作主宰、自我呈现的体上工夫。季本不仅进一步深化了阳明的这一理路,同时还从经典训释上坐实了相关思想。既然“谨独”已成为于本体上惕然用力的体上工夫,那么原本仅注重于在经验世界中对意念进行规范、落实的“诚意”工夫自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本将“意”注解为“天命流行之几”,以《中庸》“诚者自成”训释“诚”,进而将“诚意”理解为人承接天命流行而自成扩充的纵贯工夫,便是因循理论逻辑的自然结果。在这里,季本的“诚意”诠释展现出了丰富的思想史信息:一方面,季本不仅在“诚意”思想中继承了心学的义理架构,同时还在其著作中保留了其对朱子的理解和批判,因而使得我们能够从作为“德性挺立”焦点的诚意话语中更为深入地把握到理学向心学的转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经学家,季本以参经注疏的方式阐发自己的“诚意”思想,这不仅为我们基于“诚意”视点观察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细节,也为基于“诚意”视点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经学脉络。
结 语
季本对“诚意”思想的阐发体现了与理学不同的义理架构,具体表现在对“诚”“意”“独”的相关注解中。在“诚”的训释上,朱子以“实”训“诚”,在季本看来,这会造成天道与人道的二分,因而提出以“成”解“诚”,将所有工夫都收摄于内心,从而将朱子在“诚”的训释下所蕴含的分殊架构打通为一。在此基础上,季本将“物”都安置在心体的流行中,万物的生成都离不开人道的照看,因而“成物”就是“成己”,同样也是“自成”;而朱子则对“自成”“成己”“成物”有所区分,“自成”乃是天道独立运行的结果,无人道的参与,“成己”则是在人道层面而言,通过“实其心”的工夫与“实理”相合一,“成物”则是建立在“成己”的基础之上,以“成己”为前提。而对“意”,季本将朱子与阳明“心之所发”的定义改为“天命流行之几”,所谓的“诚意”工夫也就是“成就此天命流行之几”,从而将“诚意”上提至天道层面,与天命流行相接轨,“自欺”作为与“诚意”相对立的范畴乃是天命流行的阻碍;而朱子视域下的“意”作为经验性范畴有善有恶,因而需要在意念萌动之处警惕用力以防私欲干扰而陷入自欺等。同样,在“诚意”工夫中,“谨独”作为“毋自欺之要”,依旧强调在体上用功,并且同阳明一样将原本在朱子那里有先后次序的“戒慎恐惧”与“谨独”两种工夫贯通为一,强调本体之知时刻警惕警觉的同时,也防止其受到外物侵扰而为外物所诱,以保持其天命本体精纯贞一的状态。
因文章篇幅有限,注释省略,注释请参照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