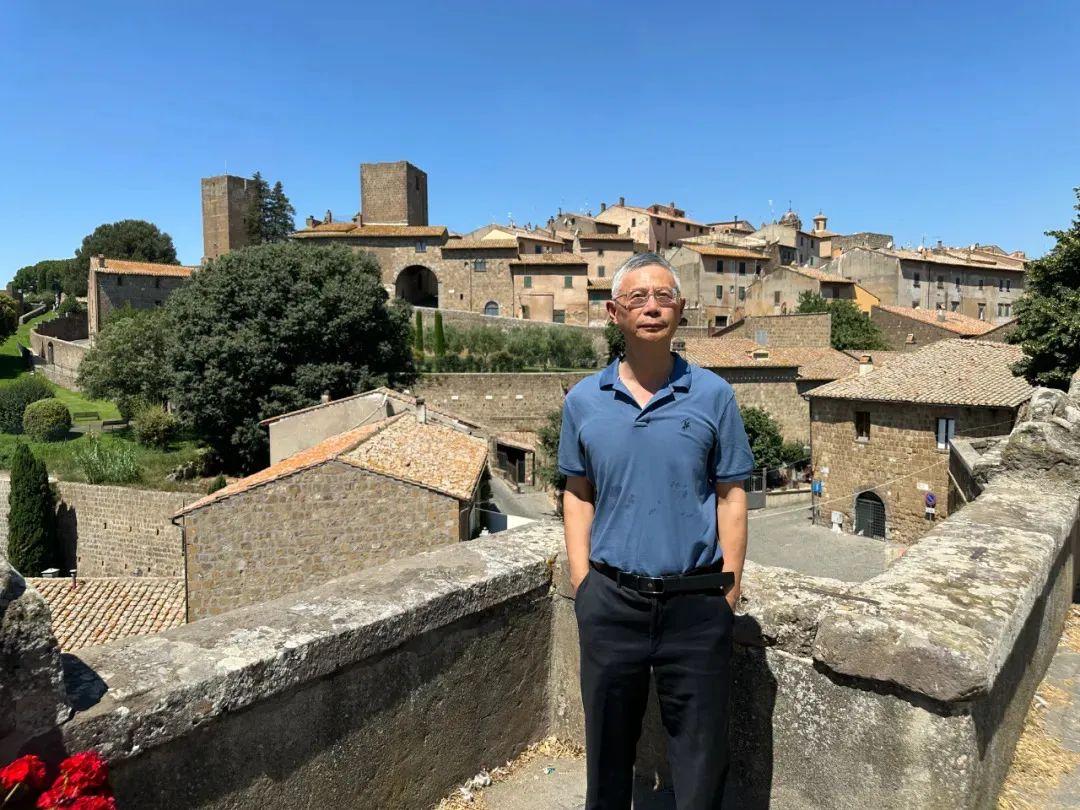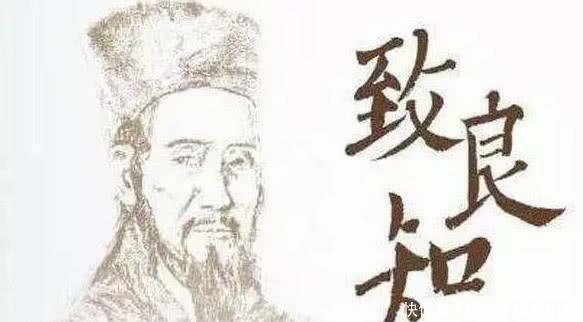试析王阳明的“说贞之道”
王永年丨福建江夏学院阳明研究院
本文原载于《中国心学(第3辑)》
明代中期,皇权专横,朝政晦暗,政治生态日趋恶化;官学与科举联袂,带来普遍性、绝对性的“天理观念”对社会生机的压抑;工商业初步繁荣,人、商品、货币流动加速,一些地区一些阶层的财富积累等因素,共同催发、激励了人的主体性觉醒与福乐期待。以“求为圣人”之志统领生活的士大夫王阳明,在上述特定背景之下,为实践“内圣外王”这一儒家确立的“整体规划”,经“龙场悟道”,开辟了“觉民行道”这一有别于“得君行道”的治平路线。[1]1515年,王阳明借为同僚之子白说取字的时机,提举、阐释“说贞之道”,将“说”确立为士子、庶民人生当有之价值,提示实现这一价值的根本依据、内在动力在于“贞”。这一重要思想渊源于孔子、孟子的“君子之乐论”,丰富了以“乐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化内核,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君子有三乐”
现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将西方、日本文化分别刻画为“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李泽厚先生则认为:“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精神是‘乐感文化’”[2],“乐感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当推儒学创始人孔子与孟子,一个并非偶然的文本事实可以为证:
《论语》开篇《学而》便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言及的内容近乎涉及儒者主要的生活,其意义与“说”或“乐”或“不愠”(亦为乐)相联。尽管三者不无差异,但大体都可归结为“乐”。尾篇《尧曰》再次谈到“乐”:“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此处则提示“公”即“公平、公正”,乃众人“说”之渊源。《孟子》开篇《梁惠王》记录了孟子谒见梁惠王讨论“利”与“乐”的言论。孟子指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意即面对同一美妙的自然景观,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享受这一种快乐,没有道德的人是无法享受的。末篇《尽心》中,孟子径直陈述“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论语》《孟子》开篇与收篇皆谈论“乐”,此种纂述确实能契合孔孟立言之价值祈向,“乐”频繁出现也可以为此佐证。快乐之“乐”字是《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之一,达24次,此外表示“喜悦”之“说”出现16次之多。《孟子》与此相似,“乐”字出现77次,快乐之“乐”达55次,“悦”字达53次。
对“乐”价值的推重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涵。孔子、孟子乐论大致可概之为以下五点:(一)“乐”是人生在世当有的价值。孔子赞誉的“说”、“乐”、“不愠”,孟子期望的“三乐”,皆是在人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即世间又超世间的生命情感,这同基督教所期求的超越此世间的天堂之乐截然不同,对这类生命情感的肯定意味着孔孟将“乐”贞定为人生在世当有的价值祈向。(二)“乐”生成的第一场域是以“五伦”关系为轴心的社会生活。“乐”只在此世间,意味着只能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的“乐”,首先或主要来源于与本己切近的人与人的交往之中。“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 “有朋自远方来”之乐、“得英才而育”之乐,显然来自与朋友、师生之和睦共在。“人不知而不愠”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也来自内省人际交往时的坦然无疚。这同决然逃离正常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试图以种种方式与某种信仰对象“神交”而获取宁静、狂喜之乐的某些宗教的主张截然不同。(三)“乐”本质是主体在内外两个向度活动中与道同在的情感体验。孔子所言之“说”、孟子所说之“三乐”,皆由“觉与习”、“教与育”“为人之道”即“为仁之道”所致。孟子所言之“一乐”、孔子所言之“乐”皆由主体笃行孝悌之道、师友之道所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赞赏的颜子之乐,在于颜子在贫贱之中不违仁德,与道同在中感受并不改其乐。“乐”与“仁”联系在一起,仁者乐,能仁便能乐。(四)“乐”重在精神上的安怡。孔孟并不排斥关联外物的感性之乐,如:由“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所体现的闭居之乐;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而来的饮食之乐等等。儒家推崇的则是在“学而时习之”或“得英才而育之”之中即在传授、理解、体悟、践行道过程中获取的乐,在“人不知而不愠”、“仰无愧”、“俯无怍”中所体证的为己之乐,其基本特质是精神性的,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乐”。这种精神性的乐是各种乐的价值级序上是最高一级,能给人带来终极的价值安顿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而西方居勒尼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青睐的,由感性满足带来的,而极易被人剥夺与消逝的“快乐”,非儒家所祈。(五)“乐”是君子当有的境界。拥有此世的、人伦的、道义的、精神的“乐”,在孔子孟子看来,它是君子的标志。清代大儒王夫之就曾指出:“‘君子有三乐’,在一‘有’字上不同。言‘有’者,有之则乐,而无之愿得有之也。父母兄弟之存,英才之至,既皆非非望之福;仰不愧,俯不怍,亦必求而后得。故当其既有,唯君子能以之为乐,而非君子则不知其可乐。然当其不能有,则不愧、不怍,正宜勉而自致。”[3]君子与非君子的重大区别在此:“君子有三乐”,“非君子则不知其可乐”。值得指出的是,“乐”作为君子境界的确立,表明儒学要求读书人、士大夫通过“学与思、知与行”来实现之。面对广大庶民而言,这自然具有导向意义,但儒家并非以此来苛求他们,基于“食色性也”,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要求居于执政、行政地位的君子,应当首先设法满足他们由安全、繁衍、富足而来的快乐的需求,其次才是教化。
二、“天下之道说而已,天下之说贞而已”
孔孟确立、阐释、践行的“君子之乐论”,对儒学尤其对宋代儒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成为道学的一个主要问题。”[4]宋代诸儒守持了孔孟“君子之乐论”的基本观念,并与时俱进,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第一,“学而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5]被誉为宋代道学先驱、“中国人中最讲究人生艺术”的邵雍,自称“安乐先生”,并将其居所冠名为“安乐窝”,身体力行“快乐哲学”。他演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明确将“乐”提撕为“学”之目标。第二,“孔颜之乐”成为理学讨论永恒的议题。自宋代道学开创者周敦颐、经两程子将人对乐的追求导向“孔颜之乐”。“乐”虽有“心体之乐”“生机之乐”“体知之乐”种种面向,但就其“乐”之倾向而言是向内收敛,更多关乎身心的内圣之乐。南宋儒者罗大经的这番话表明了这一特点:“学道而至于乐,方是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丧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6]第三,将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乐”发展为“与物同体”之乐。孔孟把“乐”理解为本己行道之后的情感体验,即把道看作“乐”之本源。这道在孔孟那即为“仁”。程颢将“孔颜之乐”之本源的“仁”作了更深的开掘:“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而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已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7]其意思是说:天、地、人原来是浑然一体、休戚相关的整体。当人真实感觉到自己与人、与物同体,那便是反身而诚,就有最大的快乐。如果我与人、与物“有对”,即反身未诚,怎么会有“乐”?由此看来,“浑然与物同体”即“仁”是“乐”之本源。它表明“与物同体”之存在本相在生活中呈现,主观体验必然为“乐”。第四,明确指示出寻“孔颜之乐”的路径为“博文约礼”或“克己复礼”。
孔孟、宋儒之乐论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明代士与士大夫。“自六世祖以来,王阳明的家族之‘乐’一直便在五伦的从游之乐与隐逸之乐之间游弋。”[8]王阳明的好友右副都御史白圻将儿子命名为“白说”。这显然寄托了白氏家族的志趣与对后生的期待与祝福。在白说成人时,白圻邀请王阳明参加其子的冠礼。礼仪完成后,白圻又请王阳明赐字以教。王阳明慎重地为其取字并撰写《白说字贞夫说》,“说贞之道”由此应运而生。时在“龙场悟道”后八年,致良知话头提出前四年的正德十年即1515年。
《白说字贞夫说》继承、发展了孔孟周程之乐论,以简洁的语言,锻制了思想内涵丰富、体现时代精神的“说贞之道”:“天下之道,说而已;天下之说,贞而已。”[9]《集韻·祭韻》:“说,悦也。”朱子注《论语·学而》“不亦说乎”之“说”为“悦”。韦昭注《国语·吴语》“诸侯必说”之“说”为“乐”。“悦”、“乐”大体相通,意思为高兴、愉快、快意、喜畅、欢欣。“天下之道,说而已”,将整个道的论述染上了“说”(“悦”“乐”)的底色。毫无疑问,天下之道涵括了天地万物,“天下之道,说而已”无非是说:天、地、人及万物之生存、运行、活动、变化其基调就是“说”(“悦”“乐”)。
“天下之说”何以可能?何以实现?或曰“天下之说”根据何在?通过何种路径得以达成?王阳明的回答斩钉截铁、一言道尽:“贞而已”。就是说,天将天下万物之内在目的或理想归宿设定为“说”的同时,也给定了指明实现“说”的根据与路径,这便是“贞”。惟有“贞”,才能实现、守持、葆有“说”。“天下之说,贞而已”这一命题,表明“贞”对于实现“说”之根据、路径的决定性、普遍性、唯一性。至此,“道”之核心要素或内在规定已呈现出来。“天下之道,说而已”,“天下之说,贞而已”可以统而言之:“说贞之道”。
对此,王阳明作了论证:“乾道变化,于穆流行,无非说也,天何心焉?坤德阖阙(“阙”当为“辟”——引者),顺成化生,无非说也,坤何心焉?仁理恻怛,感应和平,无非说也,人亦何心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按照它内在之道无穷变化,和畅谐欣流行,无非是为实现“说”而已。除此之外,天还有什么其它祈求吗?地按照它内在之道不断开合,顺遂化生万物,无非是在实现“说”而已。除此之外,地还有什么其它意愿吗?人亦按照其内在之理,恻怛友爱,与物感应和平,无非是在实现“说”而已。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其它趣向吗?这些论证自然不宜作为“外延真理”或“科学真理”来看待。他是以“启发语言”表述“内容真理”或“人文真理”。王阳明是在“天人合一”思想传统背景下,以“人化”方式,将乾之“于穆流行”、坤之“顺成化生”之自然、自由、和畅状态即“说”确认为“天极”(“天道”“乾道”)、“地极”(“地道”“坤道”)运行的根本性状,进而下贯于“人极”(“人道”),天地人“三极”成为“说乎说乎”之三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天下之道的“说”,在天、地、人三极展现为不同形式:“于穆流行”“顺遂化生”“感应和平”。用牟宗三的话说,“于穆流行”表现了“天道”的“创生原则”,“顺遂化生”体现了“地道”的“终成原则”,“感应和平”则体现人之与天地万物的“感通原则”。三者是“天命之性”下贯落实之本然性状。天依“乾道变化”,地依“坤道阖辟”,人依“仁爱恻怛”感应外物。“说”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但其本质则是共同的,即天、地、人按内在的“道”或“理”生存、生活,这即是“贞”。由此,王阳明断言:“天下之说,贞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那么,“贞”“说”关系究作何解?为何可将“天下之说”归结为“贞而已矣”?
三、“贞者说之干”,“说者贞之枝”
“说也者,情也。”王阳明以“情”来界定“说”,“说”属于“发用”的范畴,其“体”自然是“性”。“贞乎贞乎,三极之体”,“说乎说乎,三极之用”,显然天地人三极之“说”均是“贞”这一“三极之体”之发用流行。离开这个“贞”之体,“说”就会荡越无归,情肆而荡。故阳明又说:“说而不贞,小人之道,君子不谓之说也。”君子之“说”是由“贞”即性而来,是“理”之“说”。
何谓“贞”?“贞”的本义为卜问和占卜(《说文》贞,卜问也),后来引申为“正”、“固”、“定”、“当”、“干”等。[10]王阳明在“龙场玩易”期间撰写的《五经臆说》中曾诠释过贞: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而万物生,天下和平焉,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昼而夜,夜而复昼,而照临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时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复春,而生运不穷者,以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圣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复成,而妙用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贞而已耳。观夫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贞,则天地万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贞也,亦可见矣。[11]
“元亨利贞”四德对应于“仁义礼智”,王阳明于龙场悟道期间即已将“贞”视为天地人三极之“体”,“贞”对应于“智”,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阳明后来以“良知”作为“天道”“易”的代名词,在《五经臆说》中就已有端倪可寻了。昼夜交替之道(天道)、四时不忒之道(地道)与圣人赞天地化育之道(人道)都是“一贞”之道。而“天地万物之情”亦不外是此“生生不息”的贞道之体现。显然此一“贞”是统摄了“元亨利贞”四德之“贞”,是广义的“贞”。此“贞”就是性、理的同义词。“贞也者,性也”;“贞也者,理也。”王阳明以“贞”称“性”“理”,旨在展示性理之“常久不已”、流行不息而又井然有序之性质。
王阳明虽未就“性”“理”做一系统、完整的说明,但其论性首重其“本原”义,他特备看重《中庸》首章,并专门撰《修道说》发明其大义,又说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于《中庸》首章。他承继了传统儒学之天道下贯而为人性的观念:“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道即性即命”,[12]此是就天道源头处说性;而就性之彰显与落实处,阳明则说“性是心之体”,“尽心即是尽性”。[13]又说:“心之本体即是性。”[14]对于“理”,阳明则有理之凝聚曰 “性”之说,性之“条理节目”就是“理”。而理之“凝聚之主宰”就是“心”。所以在阳明心学中,性—理—心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它是人的真己,这个主宰一身的性—理—心性能够透过目、口、耳、四体发用出来,是谓“形色”,在此意义上“形色”也是天性。[15]目、口、耳、四体与形色都属于“气”的范畴,故阳明又说“气亦性”“性亦气”。另外阳明强调“性”之“超越”义,称性是“至善”“粹然至善”,它超越了善恶分别义的善,故又说“无善无恶者心之体”。[16]
既然性之“条理节目”曰“理”,“贞也者,理也”即是表明天—地—人之道本质上就是一“贞体”(“贞乎贞乎,三极之体”),并必然在其流行过程中表现出畅顺、和乐的性质(“说乎说乎,三极之用”)。 “贞”是“体”“干”,“说”是“用”“枝”。“体用一源”“干枝一体”。脱离“体”无“用”可言,脱离“枝”无“干”可言。不过就逻辑先后与价值格序而言,“体”“干”为先为重,“用”“枝”为后为轻。因此,王阳明指出:“故天得贞而说道以亨,地得贞而说道以成,人得贞而说道以生”。这意思是说:上天按自身内在之“性”“理”运行,便会实现“说”,行此“说贞之道”天便亨通;大地按自身内在的“性”“理”顺成,便会实现“说”,行此“说贞之道”,大地便利成;人按自身内在的“性”“理”生活,便会实现“说”,行此“说贞之道”便畅生。这里隐约将天道、地道、人道之运行与“亨”“利”“元”联系在一起,“人得贞而说道以生”意味着心之本体(“良知”)是“元贞”之体,是“仁且智”之体。要之,天运的亨通,地道的利成,人道的真诚恻怛都是“贞之道”的体现,作为“三极之体”的“贞”是“说”的基础、源泉。
人只要守护住“贞之体”,由“理”(“良知”“天性”)贞定自家性命,君子在其生活世界中自会“感应和平”,自会体验到种种“说”“乐”:“快活”“自得”与“真乐”。“快活”系指人之心性生活的畅快与活泼,阳明有“常快活”便是工夫的说法;“自得”指人随其所处境遇(富贵贫贱、患难生死)独立自主,一依良知、循天理应对,“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真乐” 就是孟子所谓“乐莫大焉”之“乐”、“乃为大乐”之“乐”。它是人在超越我与你、人与物的隔阂,达致“与天地万物一体”时,涌现出来的“欣和欢畅”之情态,是人与天地万物完全浑然一体的无我的存在状态,是超越时空的与天地同在的“大乐”境界。此“真乐”人人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17]
“目而色也,耳而声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说也,有贞焉,君子不敢以为过也,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义而君臣也,礼而夫妇也,信而朋友也,说也,有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贞而已矣。”这里贞说对扬说让我们想起《孟子·尽心章下》性命对扬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性命之辨中,口、耳、目、鼻、四肢五者之欲是性,但有分限与品节,不能皆如其所愿(“有命焉”),故不谓之性;仁、义、礼、智、天道在人乃天之所赋,其禀赋虽有厚薄清浊之不同,但终可以通过变化气质而尽之,故不谓之命。而在阳明的贞说之辨中,口、耳、目、四肢之欲虽有其乐处(感情之乐),但过之则流于炽而荡,故必须正心养性,以性“贞”定之,是为“性其情”,纵之而不贞,则是“情其性”。仁、义、礼、信之“说”是“天乐”(“真乐”),此“说”是由“贞”而来之乐,故须推致之、充分实现之。由贞而发之说是真乐,外贞而来之说是“小人之道”。贞道落实于心则心说,落实于家、国、天下则家、国、天下说。“说”的呈现,是由“贞”而来。故“贞者,说之干也;说者,贞之枝也。”
四、“贞必说”的根据:“良知即是乐之本体”
王阳明告诫并告慰白说及天下士子,君子的使命就坚守“贞道”,养心、齐家、治国与平天下皆以一“贞”道贯之,进而实现“心说”“家说”“国说”与“天下说”。由此王阳明提出“说也,有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的修身要求,此语置换成正面肯定性语句,便 是说: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务必以“致贞”作为行为准则。如前所述,王阳明以“性”、“理”释“贞”,性理之贞与稍后几年提出的“良知”概念在内涵上是大体一致的。在此意义上“致贞”之教也就是“致良知”之教。
何以“致贞”或“致良知”就能实现“说”?以至说“贞必说”呢?《白说字贞夫说》对此尚未有系统与深入的揭示。随着“致良知”教的提出与发展,阳明正式提出“良知即是乐之本体”的主张,“贞必说”的奥秘也因此而昭然若揭了。
应对川流不息的社会生活总会生成这样那样的意念、行为动机,如何确保意念、行为动机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而实现“说”这一终极目的与价值?对于君子而言始终是修身的一项重要任务。圣贤言说、道德条规、典型事例、过往经验、权威律令自然会为人对当下意念、行为动机的审察提供指南或参照,但能不能将其作为合理性、正当性的最高准则?显然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人的意念或行为动机都是在现实生活发生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其所处的时空、所依的条件都是现实的、个别的、具体的,以至都是唯一的,而原则、条规、律令往往是抽象的、普遍的;圣言、典型、经验往往是历史、独特的,直接以它们为准则,来确认意念、言语、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是非善恶性,难免会产生捉襟见肘之感。按照“娶必告”与“葬后伐”的规则,舜将不得娶,武将不得伐。其后果将是悖逆孝与忠之天理的。王阳明“良知说”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引导人们对本已伦理与社会实践之牢固支撑的寻求,不是在外部规则与制度中,而是在本已的心或精神中。[18]在弟子陈九川苦于“难寻个稳当快乐处”时,王阳明告诫他:“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19]
良知之所以能够成为“自家的准则”,一方面是意念生发时,其是非性质良知即同时作出准确判断;另一方面,依着良知的判断去实践,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便存,恶便去”。良知兼道德判断与道德实践于一身,良知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功能,在王阳明看来是因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王阳明的作出这一论断的理由何在?在于其“良知”在存在论上与演化、建构天地万物的“气”紧密绾结在一起。“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之论断表明良知并非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意识,而首先是“精灵之气”。此“精灵之气”是由具有“生生”性之“元气”经历“最粗者”、“稍精者”、“又稍精者”、“又精者”、“至精者”等阶段,而进一步发展成就为“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即“良知”,这“良知”即“精灵之气”,一方面具有“生生的功能性”,其功能性具体表现于其感通与感应的能力(见孺子入井知恻隐);另一方面这“生生的性能”在人心这里“结穴”遂成一“自觉的生生”,一“自知自证的生生”,“精灵之气”在人心这里得到“自觉”、“自醒”,此为“存有论”的“觉情”,故能随感而应,无物不照,而任何偏离、扭曲、破坏生生之德的念头、行为,良知无不自知。[20] “精灵之气”、“生生的功能性”乃是天理。而天理之“灵明”、“明觉”便是良知。
“良知即天理”,“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王阳明先生曾以社会生活经验来印证此理。“若夫君子之为善,则仰不愧,俯不怍;明无人非,幽无鬼责;优优荡荡,心逸日休;宗族称其孝,乡党称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悦。所谓无入而不自得,亦何乐之!”[21]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何以依从、遵循、随顺良知,便得以乐?王阳明总的解释是:“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诉合和畅,原无间隔。”用阳明弟子黄勉之的话说:“人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观之鸢飞鱼跃、鸟鸣兽舞,草本欣欣向荣,皆同此乐。”[22]这里意思是说:乐是心或良知本然应有之情态。或者说“仁人之心”、“人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人在致良知过程中,良知无遮蔽,全然朗现,乐便同时油然而生。此理清代儒者戴震有过类似体验:凡人行一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必沮丧自失。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23]王阳明这里深刻指出:乐有“七情之乐”与“真乐”等层次上区别,常人与圣贤一样都可能享有。遗憾在于常人常常有了这些快乐而不自知。常人常常因其“客气、物欲”遮蔽良知,搅此和畅之气而带来许多忧苦。“自求忧苦”、“自加迷弃”的常人,尽管处在忧苦、迷弃之中,“此乐又未尝不存”,只要达到对良知的觉悟,反省自身,以至诚立身行事,真正的、本有的快乐将再现,即由忧苦重返乐之生活。
在王阳明看来:“这良知人人皆有,……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自难泯息。”[24]因着“良知即是乐之本体”,天下人只要皆致良知,便可实现“天下说”。这期待、这承诺自然不无几份浪漫,但就其理论逻辑而言是严谨的、可能的、可望的。
五、余论
1515年王阳明提出的“说贞之道”,把“说”看作天、地、人之目的或理想归宿,或终极价值,把内涵为性、理、道的“贞”看作“说”得以实现与持存的根本,把“致贞”视为实现“说”的功夫路径。四年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以更简明的话头、更深刻的内涵,统摄了“说贞之道”与“致贞”之教的核心思想,成为阳明学成熟时期的标志。尽管如此,“说贞之道”与“致贞”之教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依然值得关注:
首先我们要看到王阳明的“说贞之道”与“致贞”之教,继承了孔孟周程倡导的“君子之乐论”与“孔颜之乐论”的基本观念:“乐”为“此世间”的价值需求;“乐”首先是道德实践中的情感体验;和美的人伦关系是“乐”的主要生成场域,“乐”是君子当有的精神境界。其次我们更要注意王阳明的“说贞之道”对孔孟周程之“乐”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一)作为内在目的、理想归宿的“说”获得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的“道”的地位;(二)“说贞之道”将“说”标榜为社会成员易于接受的目的、归宿,为 “觉民行道”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受“贞”规约的“乐”成为面向包括君子在内的社会所有成员的价值指点;(三)在“性”或“理”的生成中,或良知许可下,由人之道德理性与自然本性的实现而形成的“乐”都是正当的、合理的。由此,乐的实现场域向包括经济生活、娱乐生活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场域拓展,这与更多倾向于向内收敛的“孔颜之乐”有着明显差异;(四)深刻揭示了“乐”之本源,指出“乐”由“性”或“理”而生,为“良知即乐之本体”论的提出准备了思想资源;(五)指明了“说”与“贞”在人的生活过程中的关系,与“贞”的本体地位,为君子实现“家说”、“国说”、“天下说”提供了实践指南!
王阳明弟子王艮继承了先师的上述思想与主张,对乐的诠释沿着通俗化的路子作了新的充实,创作了《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便自觉。知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鸣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25]《乐学歌》以通俗语言,传播了以致良知重构快乐人生的思想,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致良知说”、“说贞之道”中的一系列核心思想、主张,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思想家的主张大体相似。因此,雅斯贝尔斯有理由如是说:是西方文化复兴时期的一批思想家与中国的阳明先生共同开创了这个属于我们的新时代。
注释
[1] 《余英时文集》,第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56页。
[2]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01年,第1127—1128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5] 邵雍:《邵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6] 转引自朱义禄:《论王阳明与王艮、王襞之乐论研究》,《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7]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中华书局,2004年,第16—17页。
[8] 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180页。
[9] 《白说字贞夫说》,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四,第906—907页。